上次看電視的時間、場景,你還記得嗎?
95年前的今天,1926年1月27日,英國發明家約翰·貝爾德向倫敦皇家學院院士們展示了一種新型的、能夠通過無線電傳遞活動圖像的機器。這就是“電視”。人們無法判斷電視的具體誕生之日,其誕生也不是具體某個人完成的。可是95年前的今天卻讓更多人開始著迷這一組奇怪的裝置。

當代“看電視”。(圖:IC photo)
可以說,電視是發達工業文明的產物,也隨著世界逐漸步入后工業社會,而成了明日黃花,讓位給新興的互聯網。同樣地,過去在家做作業被家長警告“別看電視”,也變為“別玩手機”。有意思的是,在我們記憶里,作為家庭集體活動的“看電視”其實曾經也被認為會破壞人與人之間的連接,會影響閱讀能力和注意力。
麥克盧漢曾說:“倘若電視將要剝奪我們文明的個性,剝奪我們不同的自我,那么我們就應該關掉電視。因為就我所知,電視與西方文明的延續是不可兼容的。”但也正是他,在1967年就預言:“等到電視變為一種舊技術時,我們才會真正理解和欣賞它輝煌的性質。”現在,幾十年已過去,反而是時候讓我們真正理解和欣賞它了。不妨隨本文作者的童年記憶從電視普及之初開始。
01
“看電視”:
一種現代生活方式的興起
如今回想起來,在我小時候的記憶中,看電視本身就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現代性體驗。在上世紀80年代的鄉下,電視機仍是奢侈品,甚至光有錢都不一定買得到,還是憑票供應的。在那個年代,電視是結婚嫁妝中的“新三大件”之一。那時一臺屏幕很小的顯像管彩電也要1000多元,幾乎相當于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資,因而很多人家里都只有黑白電視,只有我爸單位里才有一臺14英寸的日立牌彩電。
即便是黑白電視,也足夠令人艷羨了,它像是鄉下孩子通往外部世界的一個入口,折射出光怪陸離的想象。最早買電視的人家很快成了新的社區焦點,很多人甚至會捧著飯碗,去鄰居家的院子里,一起看電視。后來我一個廣西同學說,在他們鄉下,一些去廣東打工發了財的鄰居,甚至還向來看電視的人收門票:每人每晚5分錢。從這個意義上說,那時的電視作為“茶室里的電影館”,確實名副其實。

黑白電視機記憶。(圖片來源于網絡,轉引自中國家電網)
和報紙不同,電視不需要發展閱讀技能,就算是文盲也能看得懂,它以令人眼花繚亂的節目編排,將鄉村社會也卷入到現代化的進程中。與此同時,它極其直觀地展現了外面的世界,激發起人們向外發展的沖動和消費欲望——至少看過的人都渴望自己也馬上賺錢去買一臺。沒幾年,我們村里家家戶戶都有了電視機,年輕人都關起門來自己看電視,原有的鄉村生活逐漸瓦解,這與社會學家的觀察一致:電視通常被認為是一種使人孤立的技術,它傾向于強化核心家庭,但代價是減少了一般的社區公共生活。
美國學者柯克·約翰遜在調查了兩個印度村莊之后,寫成《電視與鄉村社會變遷》一書,而書中的很多描述與結論,其實也同樣適用于1978年以后的中國。他發現,電視甚至改變了當地的生活節奏,“現在,鄉村的生活不再根據太陽的位置來安排,而是根據電視節目的時間表來安排”。這種新媒體尤其對孩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們的理想抱負和人生目標常常更多地反映了他們在電視上的所見所聞,而非他們從父母和祖父母那里所學到的東西”,老人從沒顯得如此落伍。村莊里有電視的人家由于接觸到新信息而與外部世界產生聯結,但沒有電視的人家卻變得更弱勢了。

聚在一起看電視的人們。(攝影:張培林)
02
電視與中國現代化進程:
從“普通話”到“民族工業”
在中國有所不同的是,電視的普及極大地推廣了普通話,如今每家的孩子都可以通過這個小盒子聽到遠比老師和父母都更標準的普通話,在這一點上,它比以前的廣播威力大得多。中央電視臺1983年正式舉辦的春節聯歡晚會——“春晚”——很快成了中國人的新民俗,十數億海內外華人幾乎每年都將這作為必看節目,這和以往彌散的民間習俗不同,真正創造出一種“全中國人一起過日子”的想象。《新聞聯播》則證明,電視使輿論全國化了,這是以前任何報紙都無法做到的。

1983年春晚畫面。
美國學者鮑大可在1980年代重訪中國后寫下《中國西部四十年》一書,他發現,電視強有力地激發和推動了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一種自我發展的意識,因為它不斷向人們展示中國如何落后于世界,使人們真正“開眼看世界”了。正因此,曾任西藏自治區副主席的楊松強調:“越是偏遠地區,越應率先發展電視事業,因為電視是改革思想觀念、縮短本地與先進地區差距的有效途徑。”
這一點在當時是不言而喻的,作為一個大國和窮國,中國電視機的普及落后于發達國家:美國電視滲透率從0到75%只用了7年;日本電視普及率在1955-1960年間就從0.9%飆升到33.2%,1970年就已高達94.7%;中國則是1970年才造出第一臺國產彩電,真正的普及晚至1990年代,而直到2000年也只有86%——但已高于78%這個世界平均值。事實上,長虹、TCL等國產彩電在2000年前后全面“收復”市場,在當時本身就帶有象征意義,表明中國的民族工業真正崛起了,也讓國人對“中國制造”平添了許多信心。
也正因為對中國社會而言,電視本身就是極為重要的現代性體驗,而當時又普遍覺得“現代化”無論如何是好事,因此,在那種全民渴望擁有電視的年代里,國內很少出現像西方那樣對電視文化的批判性反思。相反,中國人特別愛看電視,以至于這種媒體在人們的生活中占據了不成比例的重要性:在1990年后長達約二十年的時間里,電視廣告費用占了全國廣告總額的三分之二,而在歐美日等發達國家,這個比例僅在三分之一左右。
從這一意義上說,電視的普及和更新換代,正與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同步,也是人們生活品質逐漸改善、提升的最佳縮影,象征著人們對“現代生活”的擁抱。最終,它也證明,只有當這些得到充分滿足、電視從奢侈品變為被冷落的大件家具之后,我們才能回過頭來反思,它究竟意味著什么,又曾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什么樣的沖擊。

伴隨著電視的普及,一批國產電視劇也流行開來。圖為《西游記》(1986)劇照。
03
電視威脅閱讀和公共生活了嗎?
對電視的批判,在發達國家并非新鮮事,甚至可以說從它誕生伊始就伴隨著這樣的爭議。據《美國受眾成長記》概括,這些批評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型:一是電視觀眾可能因此放棄了其他更有價值的活動;二是電視節目對觀眾具有審美的、社會的或道德的負面影響。

《美國受眾成長記》,[美]理查德·巴特蘭德 著,王瀚東 譯,華夏出版社,2007年7月。
在這些方面,首當其沖的是電視對閱讀活動的破壞性影響。德國學者本雅明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就憂慮,在電波信號“咆哮的風暴”中成長起來的孩子,“將很難找到而且也許根本找不到回到‘真正安靜的’讀書環境中去的路了”——但他那時擔心的還只是廣播、電影,還沒想到后來電視的沖擊更為猛烈。
這不算是聳人聽聞。各項研究都證明,幾乎在每個社會,人們看電視時間越多,讀書就越少。《愚蠢的白人》列出的一個重要證據,就是美國成年人年均閱讀時間只有99小時,但在看電視上卻耗費了1460個小時。
《日本大眾傳媒史》也證明,隨著電視在1955年后日益普及,15歲以上讀者的讀報時間逐漸減少:1959年每天55分鐘,1963年降至每天45分鐘,1966年再減少到每天38分鐘。在中國,1980年代曾是閱讀活動最后的黃金時期,而它如今的衰落,可想而知也始于電視的沖擊。

《日本大眾傳媒史》,[日]山本文雄 著,諸葛蔚東 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5月。
不僅如此,當電視成為家庭生活焦點之后,很快就會使之內向化了。電視的普及取代了父母與子女之間晚飯后的親密談話,使幾乎所有社會的民俗傳承變得面目全非,當一家人都目不轉睛看著電視屏幕時,家庭成員間的交流也被削弱了。路易斯·克羅南伯格有一句名言:“汽車曾誘惑人們離開家庭,而電視卻使他們回轉家庭,不過在這個過程中卻毀了家庭。”
家庭內部尚且如此,公共生活就更不用說了。社會學家羅伯特·帕特南在《獨自打保齡:美國社區的衰落與復興》一書中分析大量數據后強調:“看電視的增多意味著幾乎每一種形式公共與社會參與的減少。……電視不僅僅是社區參與度低的伴隨物,而且實際上是后者的一個原因。電視的到來所產生的一個重大影響是,所有年齡的人對社會、娛樂和社區活動的參加都減少了。電視使閑暇時間私人化了。”他的結論是:看電視是“對社會參與最具破壞性的一項行為”。
在美國,電視不僅改變了公民對政治事務的參與程度,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選舉進程和結果。很早就有人說過,像林肯這樣外形不佳、演講又長又乏味的政治人物,在電視辯論的時代是無法勝出的。著名記者哈伯斯坦在《出類拔萃之輩》中就曾語帶譏諷地說:“電視在美國政治生活中成了候選人的主要仲裁者以后,肯尼迪的形象在熒光屏上是動人的。”里根能當選總統,與他曾經的好萊塢三流影視明星身份不無關系;當然,更典型的是特朗普,他可能是第一位“真人秀”總統,電視時代最典型的特點就是極其在乎個人形象,特朗普在這一點上可謂是道成肉身。

1960年,美國總統競選歷史上第一次電視辯論。
04
當批判成為“過去”
對電視的另一大類批評,則強調它的破壞性影響:和書籍不同,它沒有門檻,無法分級,是流行文化的極好載體,但也因為這種大眾化的特質,它的信息常常是淺薄的、暴力的、誘惑的或貪婪的,往往還會對孩子灌輸社會刻板印象。中國香港作家林奕華發現,香港人關心的事情,有很多是電視臺“告訴我們的”,它尤其使“娛樂”一詞變成只有一個層次:不用腦筋,沒有品位,何必認真,無謂要求。
在內地,這樣的弊害不是沒人提過,但某種程度上正由于電視臺商業化程度并不徹底,它還沒有到“娛樂至死”的地步。歐美評論家常常指責電視上“沒有背景知識的重復指令”造成了“公眾根本性無知”,日本學者小南一郎也曾強調不應與電視臺接觸,因為“學者就是學者”,然而在中國,像“百家講壇”的火爆證明,學者不僅很喜歡電視這個新媒體傳播形式,而且受眾也把這看作是一個有效的信息獲取渠道。至少有時候,電視也確實可以成為非常有用的媒介形式。在日本,民謠自從1960年代搬上電視之后,在全國復興,很難想象其他媒體形式能起到這么大的推動作用。

《格調:社會等級與生活品味》,[美] 保羅·福塞爾 著,梁麗真 等譯,后浪丨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2月。
盡管《格調》一書嘲諷,“越靠近下層,電視整天開著的可能性就越大”,把它看作是一種淺薄的大眾文化,但不可否認,電視強有力地推平了雅俗文化之間的壁壘。它是一種文化快餐,對效果的評估則取決于收視率,促使人們關注數量多過質量,但這本身就是現代精神的本質特征之一,即便到了互聯網時代仍是如此。
在電視時代,有句話說,“電視制造一個社會的靈魂”。不論好壞,電視實現了以往通俗文學、報紙雜志都不曾達到的程度,它使大眾文化真正深入到千家萬戶,通過這種全新的媒介形式傳播信息和理念,潛移默化地形塑人們對外部世界的想象和對一系列問題的看法,因為很多人都相信,凡是電視上呈現的就是真的。
如今,網絡技術的發展,在短短十年間就擊敗了電視曾有的霸權,它對年輕一代來說可能已不再是生活的焦點,而變成了一種備選項。
1962年,當電視在美國剛剛普及還沒幾年時,電影《滿洲候選人》里的主角曾有一句頗具預見性的臺詞:“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一進房間便打開電視,另一種是一進房間便關掉電視。”五十年后,這番話似乎變得更耐人尋味了,這兩種人之間的差別也變得更為明顯了;但在越來越多的人關掉電視之后,網絡又會把一個社會的靈魂塑造成什么樣呢?
編輯:李耀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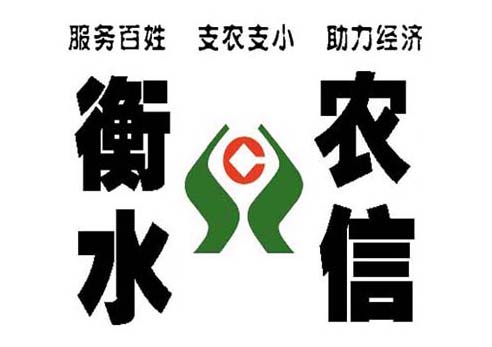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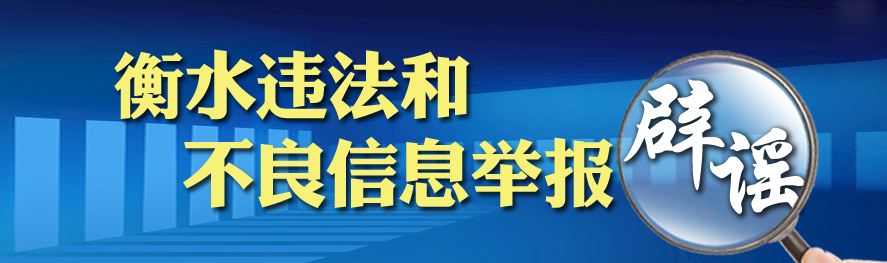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