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冀州古城墻風(fēng)光。 王鐵良 攝
南門(mén)外遺址懷古
1999年,冀州老城南門(mén)外
村民挖魚(yú)塘挖出驚天秘密
石器、石鑿、石球、石斧、鹿角、紅陶杯
沉睡在新石器時(shí)代文化層泥土里
這里,被命名為南門(mén)外遺址
石器與石球,通體磨光
雖然原始,簡(jiǎn)單,拙樸
卻是人類(lèi)進(jìn)化的標(biāo)志
冀州史前文明,破土而出
想象著,先民們身著樹(shù)皮衣
手持石器、石球,捕魚(yú),狩獵
用奔跑證明叢林里最簡(jiǎn)單的法則
追逐一頭麇鹿
食盡其肉,留下其角
被時(shí)光凝固成無(wú)言的化石
古樸而蒼勁的石鑿石斧
平面略呈梯形,橫斷面為橢圓形
砸向石頭,撲撲冒出火星
留下頂部及圓弧刃的殘缺
人類(lèi)學(xué)會(huì)制造和使用工具
才使得人類(lèi)脫離了動(dòng)物群落
那只紅陶杯,泥質(zhì)夾砂
圓唇,敞口,頸部微束,深腹,平底
像個(gè)新石器時(shí)期的古典美人
多少愛(ài)美之人艷羨的目光
被石化成通體的手指壓痕
其實(shí),所謂冀州南門(mén)外遺址
就在我如今居住的安居小區(qū)之下
一把石斧,拍打著史前的波濤
在荊棘亂石中磨礪
劈出九州之首的龍脈經(jīng)絡(luò)
冀州古城墻聽(tīng)風(fēng)
一部《冀州志》
再厚,也厚不過(guò)
冀州古城墻上的一塊磚
一段風(fēng)起云涌的歷史
再沉,也沉不過(guò)
古城墻磚縫里風(fēng)的一聲嘆息
站在荒草寂寂的古城墻上
頓感夕陽(yáng)落幕,林木蕭蕭
歷史的云煙從黃土里奔跑出來(lái)
想當(dāng)年,太守任光打開(kāi)城門(mén)迎納劉秀
也打開(kāi)了一個(gè)朝代的大門(mén)
從此開(kāi)啟“光武中興”歷史新紀(jì)元
袁紹坐冀州,風(fēng)吹旌旗獵獵
千頃洼操練水軍,“南向以爭(zhēng)天下”
最終擊敗公孫瓚,躍居中原首強(qiáng)
刺史山濤堅(jiān)守其節(jié),雅操清明
身在竹林,心和竹子一樣清醒
留下竹林寺,常常讓冀州人念起
從冀州知州任上走出的李秉衡
受命危難,領(lǐng)四軍,痛擊八國(guó)聯(lián)軍
“固知必不能敵,誓以一死報(bào)耳”
清光緒年間,冀州知州吳汝綸
以文化筑城,延續(xù)綿長(zhǎng)之文脈
吳公渠惠民,千頃洼聯(lián)通滏陽(yáng)河
城墻很厚,箭射不穿,刀砍不動(dòng)
沒(méi)有軟弱的戰(zhàn)士
只有軟弱的王朝
冀州古城墻,一根歷史的骨頭
一段永不風(fēng)化的往事
一條系在歷史腰間的腰帶
李三娘石磨傳奇
來(lái)自漢代大山的一塊石頭
讓比石頭更堅(jiān)硬的老石匠
生生劈成了兩半
一半是太陽(yáng)的圓,一半是月亮的圓
天造地設(shè)的吻合,同軸,同步
石磨合上,便有五谷雜糧溢出
仙女李三娘谷子一樣低著頭
雙日,于城外海子磨面
單日,為城內(nèi)百姓送面
她不愿助袁紹興兵,奪取天下
聞金雞叫,遂騎神牛騰云駕霧而去
奔向泰山,從此再也沒(méi)有回來(lái)
從兩漢到隋唐,從宋元到明清
石磨在春夏秋冬中轉(zhuǎn)動(dòng)
如今,靜靜躺在博物館里
地上,大石磨不說(shuō)話
地下,老石匠沉默
只有李三娘,依然活在冀州人心間
在老鹽河,我感受到黃河的脈搏和心跳
河流出發(fā)時(shí),就注定不再回頭
不管如何改道,也要奔向大海
那奔流不復(fù)還的倔強(qiáng)和豪情
足以從天上抵達(dá)人間
黃河也曾北流
也曾滋潤(rùn)過(guò)棗強(qiáng)、信都、衡水的土地
河水向北沖擊,打開(kāi)河道
七個(gè)“開(kāi)河”老村的遺跡,至今清晰可辨
兩岸聚集著樸素的村落
收留下多少艱辛與苦難
有故鄉(xiāng),有炊煙
有高高的蘆葦和長(zhǎng)長(zhǎng)的思念
南宋建炎元年,北流黃河終斷
改南流,轉(zhuǎn)東流,入黃海
黃河水不再恩澤衡水
漸漸,河底積聚起厚厚的鹽堿
幸好,這里沒(méi)有被漳河或者
其他河流侵占和沖刷
從此,黃河故道變身老鹽河
一群將黃土穿成衣服的人“淋小鹽”
傳說(shuō)中那十八只木船上的鹽
都融化在這條大渠里
“南田”“北田”“王家口”“李家口”
這些浸透鹽味的村名依然新鮮
老鹽河,歷史遺留在衡水的一段記憶
有著黃河的脈搏和心跳
原來(lái),我們也在母親河的懷抱里啊
曾經(jīng)那么近,又那么遠(yuǎn)
吳公渠,一個(gè)教育家的治水往事
上古,大禹治水自冀州開(kāi)始
晚清,吳汝綸也在冀州治水
是上天的約定,還是歷史的契合
贏得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禮贊
你引千頃洼之水,入滏陽(yáng)河
浩浩蕩蕩,自南而北,帶我們飛
把一個(gè)教育家的血脈融化進(jìn)去
彈奏出亙古未聞的和諧樂(lè)章
飄揚(yáng)的名字,流動(dòng)的曲線
沿著青筋暴凸的手臂蜿蜒而行
龍行大地,一路灑下福祉
千畝斥鹵之地,變?yōu)楦嚯榱继?/p>
今天,我在吳公渠上懷念吳公
感嘆人與水的生動(dòng)切磋,相互給予
吳公閘如一位老者端坐在入口處
看千頃之水,怎樣涌入河的臂彎
人說(shuō)“奇跡無(wú)法復(fù)制”
我雖不肯相信,卻也信心滿滿
當(dāng)年吳公的子民,在與大自然對(duì)決、博弈之后
又回到對(duì)大自然的感恩和敬畏
夕陽(yáng)用一雙筷子夾住吳公渠
卻舍不得一口吞下這斑斕的美
兩岸的翠綠紅紫,隨流水一路奔突
一群野鴨在開(kāi)闊處,叫得天高水遠(yuǎn)
吳公渠,一枚流水收藏的書(shū)簽
銘記著一個(gè)教育家的治水往事
脈管中的血液依舊喧響
在歲月的長(zhǎng)河里,波光瀲滟
作者:楊萬(wàn)寧 編輯:李耀榮









 廣告
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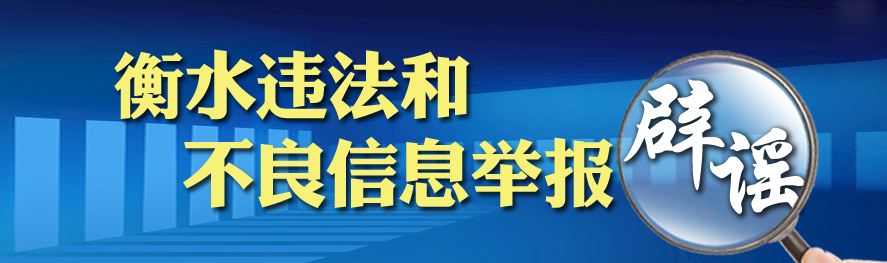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