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薰風起,盎然入夏來。漫步在家鄉的大街小巷,看到一個個碌碡一聲不響地躺在墻角一隅,仿佛睡著了似的。但它們筋骨猶存,依舊是那樣挺脫、圓潤、結實,默默地安臥在晨風中,進入了恬靜的休閑時光。
掐指一算,這些碌碡退休也快三十年了吧!想當年,它們一個個威風凜凜,被高頭大馬,抑或健壯的黃牛,甚至是馬力強勁的拖拉機拖著,在打麥場上碾來碾去。
“吱吱呀呀”,和火熱的空氣交織在一起,回響在打麥場的上空。小麥連稈帶穗,平鋪在寬闊的場院上,被炙熱的太陽曬得蓬蓬松松。大碌碡碾壓過來,渾圓的麥稈慢慢被壓扁了,漸漸由黃變白,成了光溜溜的麥秸。鼓鼓囊囊的麥粒,被碌碡碾壓下來,和麥秸、麥糠混在一起。碌碡越轉越快,麥秸越壓越平,在老鄉們的吆喝聲中,碌碡收攏翻滾的腳步,告別夏日最火爆的舞臺。
芒種又至,收麥都機械化了。這些碌碡功成身退,靜臥墻角,成為老鄉們小憩的坐物。夜色闌珊,熱氣未消,老鄉們端坐碌碡之上,談論著感興趣的話題,那氣氛比夏日的空氣還熱烈。碌碡上卻涼氣頻發,令坐者不躁不熱,頗感舒適。因此總有老鄉惦念著碌碡,匆匆吃過晚飯,便來此坐定,愜意地等著聊友。一位老鄉在碌碡上坐久了,也會有其他老鄉提出輪流坐莊,共享清涼之福。那些關于碌碡的話題,老鄉們百談不厭。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農村缺少娛樂設施。農閑時節,一到傍晚,年輕人不約而同,齊聚場院,紛紛玩起推碌碡、蹬碌碡、戳碌碡的游戲。推碌碡最為簡單。推者彎下腰,雙手使勁兒推碌碡,待碌碡緩緩啟動,便兩手交互替換,單手持續加力,越推碌碡滾動越快。推者駕輕就熟,甚至可以跑起來,簡直就像推風轱轆一樣。蹬碌碡最講技巧。一個人先用腳蹬動碌碡,然后趁勢站到碌碡上,雙腳交互用力,踩動碌碡,或臉朝前,或面沖后,但身體需保持平衡。碌碡滾動自如,蹬者越踩越輕快,還可以表演吹笛子等才藝呢!戳碌碡可是個力氣活。碌碡平躺在地上,戳者貓腰撅腚,雙手捧定碌碡一頭的底面,然后呼吸提氣,陡然發力,拼命向上抬起。戳者一鼓作氣,甚至大喊一聲,碌碡就被穩穩地豎起來了。些許游戲,老鄉們說得頭頭是道。現在想起來,既令人不可思議,又讓人忍俊不止。老鄉們的游戲盡管有些滑稽和笨拙,但他們以苦為樂,強身健體,我們油然心生敬畏,贊不絕口。
說起這些碌碡,可是真材實料,都是清一色的大石頭。它們家居深山,脫胎于山石,但比山石更有靈性。它們被石匠雕琢成圓柱體,或長或短,或粗或細,不拘一格,但質地堅硬,以超凡的噸位,成為鄉親們軋麥碾谷的得力工具。它們粗獷的紋理中,刻滿了生活的印記,寫盡了歲月的滄桑。它們在歲月中滾動,消磨了自己的身軀,為老鄉們奉獻了甘美的生活。
家鄉的碌碡,曾經是場院的主角,在那里大顯身手,風光一時,而今成了掛滿鄉愁的老物件,靜臥在小村的角角落落。悄無聲息的碌碡,碾過了無邊的歲月,滾過了漫長的歷程。它們是美好生活的創造者,它們是時代精神的守護神。
多少年過去了,家鄉的碌碡,依然轉動在我的心中,一刻不曾停歇。它們“石心石意”永不老,它們“石風石骨”萬古存。
作者:劉譽盛 編輯:李耀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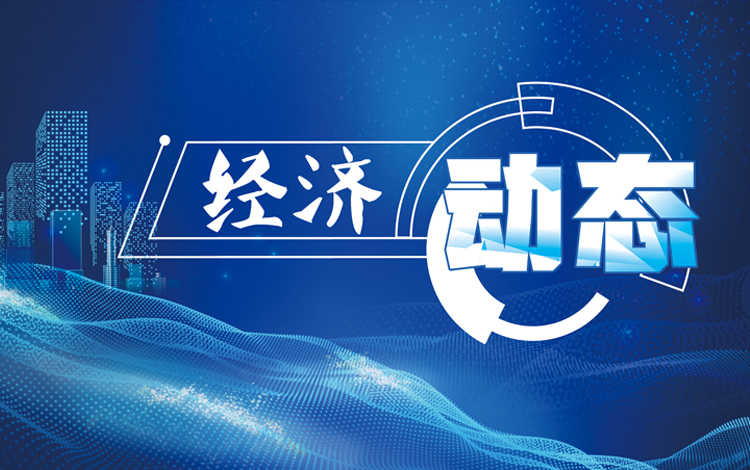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