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我們村西口兒,一直往西,過(guò)了老鹽河,便是大洼的東岸邊。大洼的歷史很悠久,能追溯到哪個(gè)年代,說(shuō)法不一。大洼也叫千頃洼。順大洼坡往下走,有很多條人走出來(lái)的小道,走得最寬的便是往西南方向的奔冀州城的一條大道。俗話說(shuō)“干走堿場(chǎng)濕走沙”,大洼是鹽堿地,春天少雨時(shí)節(jié),雖沒(méi)人工修筑,但車來(lái)人往,碾踩得平整光滑。因鹽堿地泛潮濕、路面不起土塵,也很少坑洼、車轍的痕跡。
冀州,西漢以前,都認(rèn)為九州系大禹治水后劃分,據(jù)《尚書(shū)·禹貢》記載:冀、兗、青、徐、揚(yáng)、荊、豫、梁、雍為九州。冀州乃九州之首,東漢、三國(guó)時(shí)是兵家必爭(zhēng)之地,也留下了很多故事。大洼的南岸便是冀州城,城池自漢代至今基本沒(méi)挪動(dòng)過(guò),二十世紀(jì)五十年代還有東西南北四城門(mén),且城墻、城門(mén)基本完好。
從東岸下坡往西南到冀州城最多五公里,若順繞岸大道走約有九公里,人們上城趕大集,好天好道,便走洼里這條近道。道兩邊兒,春天一望無(wú)際的是泛著白花花鹽堿的地皮,如蒙上了一層薄薄的霜雪。沿著大道兩邊兒離岸較近的平整地段,還時(shí)不時(shí)有一片片不相連接、零零散散的耕地塊兒。耕過(guò)的地不論東南西北什么方向,地塊兒也不論什么大小方圓。雨后便在地塊兒里耩一些谷子、高粱等耐旱的作物,風(fēng)調(diào)雨順,秋天就有收成。遇干旱也許顆粒無(wú)收,但那些勤快的岸邊農(nóng)民還是年復(fù)一年執(zhí)著地耕種著。這洼里的地不屬在冊(cè)耕地,屬拓荒、誰(shuí)耕歸誰(shuí),收獲多少算多少。
往大洼深處,便出現(xiàn)了一片片曬鹽池,每個(gè)曬鹽池大小不一,大都像農(nóng)家院兒那么大。鹽池用白灰和泥土夯實(shí),周圍圍上埝,再打一口小鹽井,鹽井周遭用磚砌成,直徑約50厘米,圓形,井深不足一丈。鹽水很快滲滿了井,鹽水的濃度和海水濃度差不多。把鹽水用桶提上來(lái),倒入鹽池中,鹽水有約十厘米深就行。夏天,鹽水經(jīng)蒸發(fā)和滲漏幾天,水分沒(méi)了,鹽池中留下一層小顆粒的鹽。我們當(dāng)?shù)亟行←},也叫土鹽,顏色微微發(fā)黃,賣幾分錢(qián)一斤,比供銷社的大鹽便宜一半,人們?yōu)槭″X(qián)大都吃土鹽。天氣涼了時(shí),鹽池便結(jié)成了大顆粒,晶瑩剔透的硝,舔一舔,涼嗖嗖的但不咸,行業(yè)話叫“熱曬鹽,冷出硝”,其實(shí)就是亞硝酸鹽,雖不能吃,但也不少賣錢(qián)。
夏天雨季到來(lái)了,那白花花的鹽堿地漸漸變成了綠色,各種野草野菜也都長(zhǎng)了出來(lái)。大洼中心有一條南北向的小河,那河水是淡水,一部分從上游流進(jìn)來(lái),也有一部分是雨積水,長(zhǎng)年累月在河底最深洼段存了下來(lái)。淡水也變得有些微微的咸苦味兒。人們?cè)谕堇锔苫羁蕵O了,手捧喝幾口也能解渴。河里生長(zhǎng)了一些野生的鯉魚(yú)、鯽魚(yú)、白鰱、蝦等,不下十幾種類。水多時(shí),岸邊的男人們用做窗紗的幾米長(zhǎng)紗繃子,兩頭兒綁上細(xì)竹竿就可以撈魚(yú)了。麥?zhǔn)諘r(shí)節(jié),幾個(gè)男人打伙摸黑下河。凌晨三四點(diǎn)鐘,河水很涼,齊腰深的水,抬上來(lái)的大多是小蝦米,小魚(yú)很少。天一亮再抬上來(lái)的便小魚(yú)多小蝦少了。這時(shí)要收工了,回家不耽誤下地干農(nóng)活兒,三四個(gè)男人用一兩個(gè)鐘頭撈上來(lái)的蝦,可每人分一洗臉盆那么多。小蝦不用拾掇,其中的小魚(yú)可揀出來(lái)喂雞喂豬,也可不揀出來(lái)一塊兒炒著吃或上油炸著吃,是下酒下飯的美味佳肴。
天旱雨水少時(shí),河水?dāng)嗔鳎屯莺佣渭却孀×怂擦糇×唆~(yú),水草中能抓到一二斤以上的鯉魚(yú),也有三四兩的鯽魚(yú)、鯰魚(yú)。那年代,人們舍不得吃豬肉,這些不花錢(qián)的魚(yú)蝦,豐富了人們的餐桌,也改善了人們的生活。
秋天是大洼最壯美的季節(jié)。微風(fēng)吹過(guò),它像大海一樣蕩起綠色的波浪。洼中那一片片海子一樣的水面上長(zhǎng)滿了蘆葦和蒲草,密密的草叢中傳出各種水鳥(niǎo)的叫聲,此起彼伏,像大自然的交響曲。雨水把鹽堿壓下去了,泥土變得更肥沃,草長(zhǎng)得很茂盛。深秋時(shí)節(jié),大洼中成片的鹽露菜吸足了土壤中的鹽分,變成了朱紅色。比鹽露菜高大一些的綠色堿蓬棵,稀稀疏疏地點(diǎn)綴在鹽露菜的紅色之中,增加了色彩的層次感。
鹽露菜屬什么科?學(xué)名叫什么?沒(méi)人去研究它,是不是這三個(gè)字,也沒(méi)人琢磨,反正大洼岸邊的人們一直這么叫。鹽露菜變紅了的時(shí)候也是它成熟的季節(jié)。人們開(kāi)始下洼砍割,一個(gè)人半天兒時(shí)間能砍一驢車,拉回家攤曬開(kāi),曬干垛成垛,幾車就垛一個(gè)垛。等入冬前把它堆成堆點(diǎn)著火,需有人看管,只許冒煙,不能有明火,說(shuō)是一冒明火便把其中的鹽分燒沒(méi)了。在噼噼啪啪的燃燒中,鹽露菜變成黑灰色的灰粉,把灰粉倒進(jìn)水缸大小的竹篩中,壓成中間凹、四邊高的盆狀,抬到淺水缸上。然后慢慢往灰粉上倒水,讓水慢慢地由灰粉滲到缸里。大約一天的時(shí)間,淺水缸里灰水快滿了,上面的灰粉也快干了,就用這灰水腌咸菜。灰水很咸,腌出來(lái)的芥菜疙瘩、白蘿卜、胡蘿卜有一種咸鮮香的味道,比用大鹽腌的好吃得多。人們每家每年都腌一兩缸咸菜,夠來(lái)年吃一年的。那年代,蔬菜多少不要緊,但必須保證有自家腌的咸菜吃。
那堿蓬棵也有用,像鹽露菜一樣,如法炮制,用淋出的堿水洗衣服,除油又去污,比供銷社賣的堿面兒好使又不花一分錢(qián)……
大洼,年復(fù)一年,毫不吝嗇地奉獻(xiàn)著不盡的源泉,大洼邊的人們,一代又一代依存大洼,生生不息,孕育著希望和未來(lái)……
作者:李忠慧 編輯:李耀榮







 廣告
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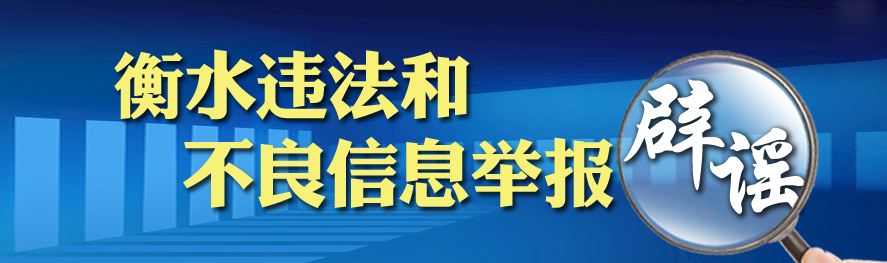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