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發(fā)現(xiàn)張姐的手串,我像見了久別重逢的親人般驚叫一聲,太漂亮了!
張姐說,你要是喜歡,就多看兩眼。
我嘴一歪笑道,以為你說,你要是喜歡,就送你啦。
張姐哈哈大笑。其他人也哈哈大笑。
這是一間茶室。張姐好客,我們幾個常來。
再聚會,我像著了魔,總想摸一摸張姐的手串。顆顆珠子紅得那么醉人,不是那種艷壓群芳的紅,而是舒服到心里的紅,看不夠。張姐呢,也喜歡我當著眾人的面夸她手串。她幾乎不怎么戴,好像就等著我去,我摸,我夸呢。
李姐說,這么喜歡,干嘛不買一串?
于是拍照到購物平臺搜索。頁面上出現(xiàn)一堆相關(guān)鏈接。和張姐這串最為相似的一串,標價兩千多塊錢。我嚇一跳,立刻覺得和這貨緣分也沒那么深厚。
張姐輕描淡寫地說,我這串還要貴一些,保山南紅啞光塔珠,看,色紅肉潤吧,這屬收藏級別。
你怎么舍得買這么貴的手串?我問她。她穿著單位幾年前發(fā)的工作服,怎么看也不像追求奢侈品的人。
別人送的。
誰送的?
她笑而不答。中年婦女的事不好老追著問。尤其,她還是個眉眼好看、滿腹詩書的寡婦。
大概在第十三次或第十五次聚會時,我照例把玩手串,她們照例喝茶、暢談文學。后來我去了趟洗手間,回來坐下再沒動手串,我好歹也是個文人,多少得說兩句酸了吧唧的話。
茶話會散了大概半小時,小群里張姐圈我:“俠妹,看見我手串了嗎?”
“就在你寫字臺上。
怎么,沒啦?
不可能,當時我還盤了好一會兒呢。你再找找。”
“從你們走了就找,怎么也找不著,屋里家具都挪兩遍了。”
我一聽慌了,不用說,我分明是第一嫌疑人呀。
我說:“你等著,姐,我這就過去。”話畢,我把自己的背包里里外外翻了個遍,又驗了胳膊,查了衣兜,這才確信手串不在我這里。
到了茶室,我瞪起300多度大近視眼,拉開地毯式搜索。結(jié)果只搜出個寂寞——張姐平時的笑臉早已陰云密布,眼睛里寫滿懷疑,房間里全是我倆相互埋怨的喘氣聲,本來到了午飯時間,誰請誰呀?誰吃得下?
忘了是怎么不歡而散的了。回家后我又畫蛇添足在群里問了句,兄弟姐妹們,是不是誰跟張姐開玩笑藏起來了?這種玩笑可開不得呀。
群里像都死了般。
我平時干嘛那么手欠?這倒好,文友們一定懷疑我呀,我都懷疑我是小偷。
一下午我都活在糾結(jié)中,給張姐買一串吧,冤死了。不給張姐買,怎么像欠了她。
文友們誰能證明我的清白。忽又想,張姐是不是賊喊捉賊。不,如果她討厭我,不想讓我去茶室,就不會每次電話相約。
那就是某位文友偷了張姐的手串,反正有我背黑鍋,正好栽贓。誰呢?可真是氣死個人。我開始挨個尋思。越尋思越覺得,他們個個是賊。
臨近黃昏,張姐來電話說:“魏東俠,你再找找,你那兒到底有沒有?會不會拿錯?”
交情到這兒,也就沒什么可說的了。
晚上睡不著,隨手打開朋友圈,張姐發(fā)布的幾張圖片映入眼簾,我頓感后背發(fā)涼。今兒下午他們又聚會了。又聚會沒什么,關(guān)鍵沒叫我。這可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一股羞憤之情涌上心頭。他們在一起會說什么呢?
能說什么?
我真想一氣之下把自己的手剁下來喂狗,氣性再大點,我都不想活著了。
一夜無眠,徹底明白了死不瞑目的感覺。
一上午痛苦。痛苦一下午。
又到夜里了,還是睡不著。
忽然,電話響起。張姐。
我猶豫著接還是不接。終是接了。
“俠妹,找到了找到了。”
“啊?”
“嗨,原來就在我胳膊上,好久不戴,都忘了這是胳膊上的玩意兒了。這說洗澡才發(fā)現(xiàn),真是虛驚一場。”
天哪!我?guī)缀跻蕹雎暳耍底园l(fā)誓,以后碰到別人再好的東西,也絕不多看一眼,更不會隨便動一下。
作者:魏東俠 編輯:李耀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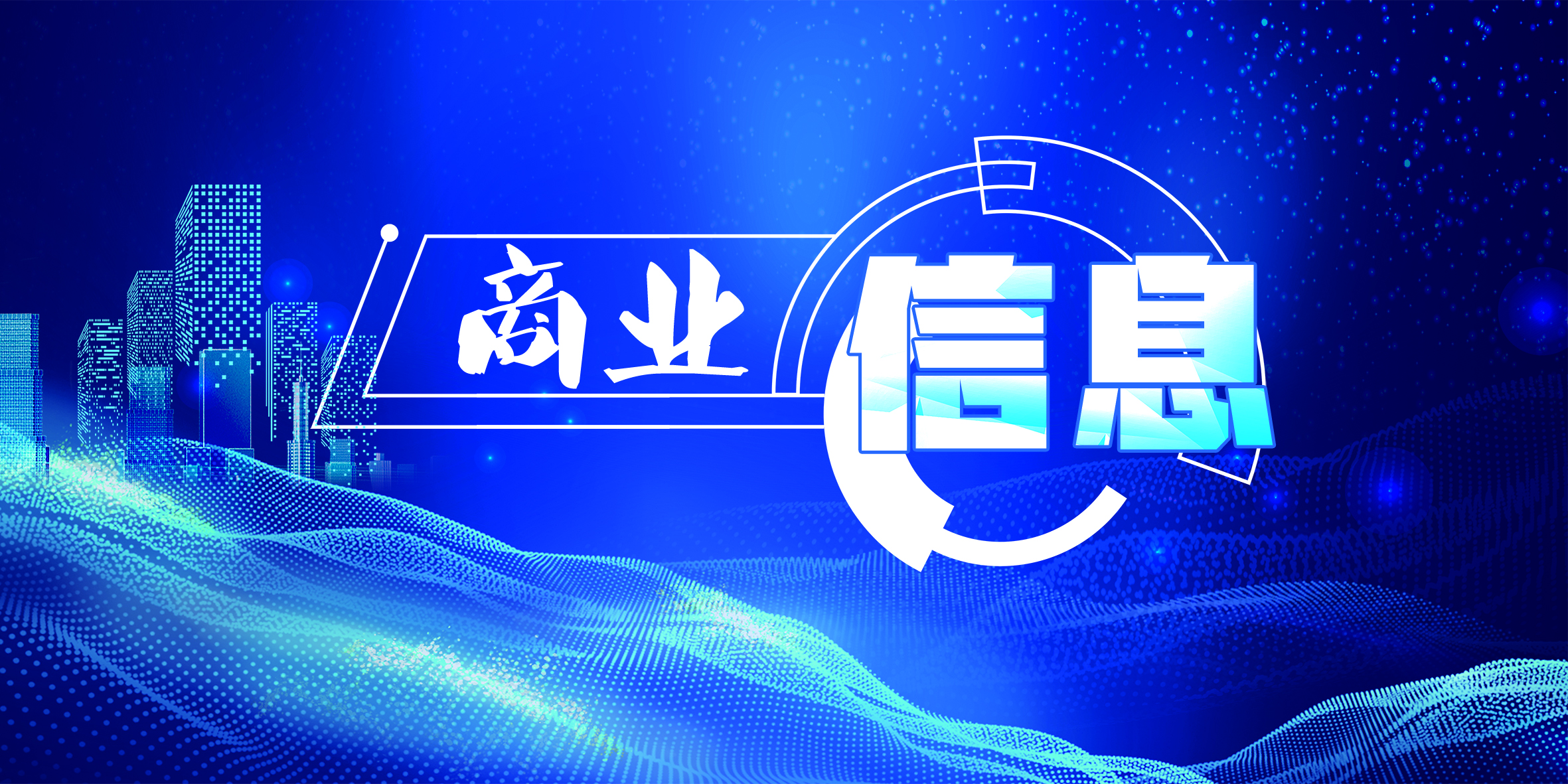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