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gè)民族內(nèi)部,為了產(chǎn)生一位天才,總是需要幾百萬(wàn)人。一個(gè)真正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時(shí)刻——一個(gè)人類(lèi)的群星閃耀時(shí)刻出現(xiàn)以前,必然會(huì)有漫長(zhǎng)的歲月無(wú)謂地流失。”
這是斯蒂芬·茨威格在《人類(lèi)的群星閃耀時(shí)》序言里寫(xiě)的一段話(huà)。在這本書(shū)里,他用十四個(gè)歷史故事講述了十四個(gè)創(chuàng)造和決定歷史的時(shí)刻,包括太平洋的發(fā)現(xiàn)、拜占庭的陷落、拿破侖的滑鐵盧戰(zhàn)役、列寧的十月革命、《彌賽亞》的創(chuàng)作、《馬賽曲》的誕生、歌德的《瑪麗恩巴德悲歌》、黃金國(guó)的發(fā)現(xiàn)、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刑場(chǎng)瞬間、越過(guò)大洋的第一條海底電纜、離家出走的托爾斯泰、人類(lèi)第一次南極探險(xiǎn)、守望共和的西塞羅之死以及威爾遜的夢(mèng)想和失敗。
歷史人物無(wú)疑都是天才。他們不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但在關(guān)鍵的時(shí)刻會(huì)決定歷史的走向。茨威格筆下的歷史人物,不是高在天上,而是就在人群當(dāng)中,在他們身上既閃耀著偉大人物的人性光輝,也有普通人身上的世故和懦弱,甚至?xí)腥诵灾辛钊瞬积X的惡。巴爾沃亞在發(fā)現(xiàn)“南邊的大海”(太平洋)的前夜,用慘無(wú)人道的殘酷玷污了自己的名聲:他將一批失去反抗能力的印第安人俘虜縛住手腳,讓一群饑餓的狼狗撕咬、吞食,在他名垂青史的同時(shí)也使他遺臭萬(wàn)年。奧斯曼帝國(guó)的蘇丹穆罕默德二世在1453年5月29日攻占了拜占庭,標(biāo)志著東羅馬帝國(guó)的滅亡,歐洲歷史揭開(kāi)了新的一頁(yè)。然而,也是在勝利的前夜,他向士兵許下了可怕的誓言:在攻克拜占庭城以后允許部隊(duì)官兵盡情劫掠三天,家什器具、金銀珠寶、男人女人和孩子,一切都屬于打了勝仗的士兵,而他本人將放棄這些東西,他只要征服東羅馬帝國(guó)這個(gè)最后堡壘的榮譽(yù)。他完全兌現(xiàn)了承諾,甚至連圣索菲亞大教堂也沒(méi)有幸免于難。攻占拜占庭給他帶來(lái)無(wú)上的榮譽(yù),也給他帶來(lái)難以磨滅的恥辱。在茨威格筆下,古羅馬政治家、思想家西塞羅作為共和政體的捍衛(wèi)者被專(zhuān)制獨(dú)裁者殺害時(shí)的悲情,美國(guó)總統(tǒng)威爾遜追求人類(lèi)永久和平的政治理想遭遇舊歐洲道德墮落抵制時(shí)的落寞,亨德?tīng)杽?chuàng)作《彌撒亞》時(shí)帶來(lái)的肉體和精神的復(fù)活,以及年邁的歌德接受年輕的烏爾麗克擁吻時(shí)令他難以忘懷的心情激蕩,都是那么鮮活生動(dòng)。
歷史發(fā)展有它自身的邏輯。我們更多地關(guān)注群星閃耀,關(guān)注高光時(shí)刻,但高光和群星背后則是漫長(zhǎng)歲月的等待和前赴后繼的探索。歷史事件都有偶然性,但偶然性背后有必然性和確定性。奧斯曼帝國(guó)雖然強(qiáng)大,穆罕默德二世帶領(lǐng)部隊(duì)圍攻一個(gè)多月,特制大炮在外城墻上轟炸了無(wú)數(shù)個(gè)大洞,仍然對(duì)攻進(jìn)拜占庭城束手無(wú)策。如果不是那扇供行人通過(guò)的小城門(mén),如果這扇小城門(mén)沒(méi)有被東羅馬士兵忘記,如果土耳其禁衛(wèi)軍沒(méi)有發(fā)現(xiàn)這扇小門(mén),那么,拜占庭的命運(yùn)會(huì)不會(huì)改變?這扇叫凱爾卡門(mén)的城門(mén)改寫(xiě)了歐洲乃至世界的歷史。但是,歷史沒(méi)有如果。拿破侖和威靈頓的部隊(duì)的滑鐵盧戰(zhàn)役,我們看過(guò)無(wú)數(shù)次的描述,這次戰(zhàn)役像一部扣人心弦的戲劇,雙方不斷變換著有利位置。如果拿破侖不是重用了格魯希,如果格魯希的部隊(duì)能夠及時(shí)過(guò)來(lái)增援,固執(zhí)又平庸的格魯希一分鐘的考慮改變了拿破侖和世界的命運(yùn)。但是,歷史沒(méi)有如果。
也許,西塞羅、拿破侖等這十四位歷史人物應(yīng)該感謝和茨威格的“遇見(jiàn)”。茨威格就像他們的知音,走進(jìn)了他們的內(nèi)心,走進(jìn)了他們的故事。他不是一個(gè)旁觀者,更像一個(gè)親歷者。茨威格讓他們從偉大走向平凡,又從平凡走向不朽。那么,他們之間的“遇見(jiàn)”呢?是偶然,是必然,還是偶然之中的必然呢?
作者:李增軍 編輯:李耀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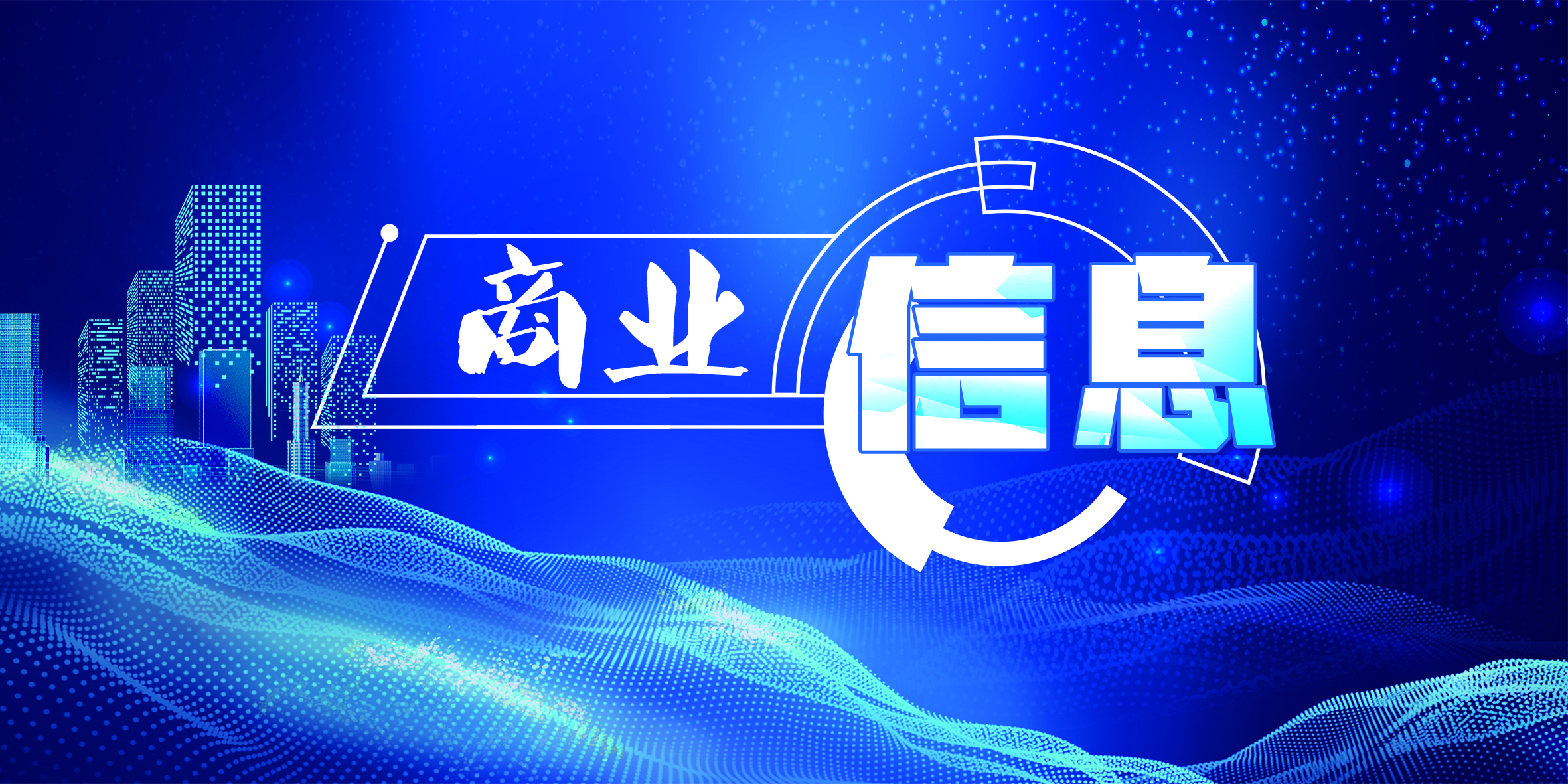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