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有一只藍邊的大號白粗瓷碗,稱為白碗。這個碗是父母和奶奶分家另過時,奶奶分給的。父親從小個子高、飯量大,奶奶怕父親撐著,每頓飯前都讓父親先用這個碗喝上半碗剩飯。
冬天里炒了白菜、夏天里拌了黃瓜,母親都裝在這個大碗里,一家人圍著吃。幾年后,大碗裂了一道深紋,村里來了鋦盆鋦碗的小販,母親把這碗拿出去鋦了兩個鋦子,鋦得嚴(yán)絲合縫。又堅持用了好多年,直到父母去世,這個大碗還在。
我小時候用的是一種深褐色的粗瓷碗,我們稱為黑碗。冬天的紅薯凍過后,母親也舍不得丟掉,仍然煮到粥里去,外皮也不切去,凍過的紅薯雖然不好吃,粥卻是甜的。那時候我身體孱弱,經(jīng)常生病,母親經(jīng)常從村醫(yī)處開來藥面,在黑碗里用水和過,用小勺喂給我吃。藥面那么苦,我不肯張嘴,母親急得把我抱在懷里,一手捏著我的鼻子,一手往嘴里灌藥。我的小腿彈蹬不止,大哭不止,藥就在我張嘴哭的瞬間灌了進去,母親和我一人折騰出了一身汗。事后母親給親戚介紹經(jīng)驗說,小孩感冒灌藥最靈了,折騰幾次出幾身汗,再加上藥力作用,很快就能好。
分田到戶以后,家里種植了幾畝棉花,拆換棉衣棉被續(xù)進了一些新棉花,舊的老棉花套子和舊布鞋母親積攢起來,大約攢了一年的時間,秋后,推著獨輪車換花碗花盤子的小販開始走街串巷,撥浪鼓一響,婦女們圍攏過來,有換盤子換碗的,有看熱鬧的。
母親把塞滿雞窩的老棉花套子和舊布鞋都拿出來,小販過秤后,讓母親挑四個花邊的茶碗。母親把襖袖子挽了挽,生怕肥大的袖口蹭碰碗盤。她拿起這個看看,拿起那個敲敲,那茶碗就大小兩個型號,花色略有不同,母親卻是非常看中這個挑選的機會,挑的茶碗不能有一星黑點。最后母親心滿意足地挑了四個大號的茶碗喜滋滋地拿回家來。不忘對我們說:“以后有廢品可得攢起來,能換花碗花盤子呢。”此后,我就留意街邊的垃圾,哪怕是一片碎布條我也要撿回家來。
換了幾年后,家里有了一摞白粗瓷碗,鑲著藍邊,還有幾個比碗口略大的花盤子,這盤子平時基本不用,只在過年過節(jié)家里來客人時才擺上。這些盤子碗母親用了一輩子。
后來家里開小吃部,弟弟專門買回了相應(yīng)尺寸的細瓷盤子和碗,母親卻從來不用那個吃飯,覺得那是金貴的餐具,是用來掙錢的工具。她還是習(xí)慣用以前的粗瓷碗。村里換盤子換碗的越來越少,母親還是又換回了幾只碗,帶著紅花的碗,雖然也是粗瓷,但看上去美觀了不少。母親換了一只大號的紅花碗,端在手里沉甸甸的。那幾年我胃口一直不好,面黃肌瘦,回老家時母親總是讓我用碗帶回調(diào)好的肉餡或煮好的餃子。我的碗櫥里陸續(xù)積攢了好幾個母親的粗瓷碗。一次母親來縣城看我,用大紅花碗裝了一碗調(diào)好的肉餡來,并執(zhí)意把碗留下,命令我說:“你太瘦了,以后吃飯就用這個大碗。”我從內(nèi)心對這個大碗是嫌棄的,總覺得自己住進了高樓,買了細瓷的小碗,這個大粗瓷碗與我的生活格調(diào)格格不入,它太土氣了。但是我拗不過母親,只好留下。沒想到隨后的歲月中我慢慢接受了這個大碗,因為無論是盛湯還是撈面條,這個大碗都非常順手,吃飯也非常過癮。
如今母親過世已滿10年,母親的幾個粗瓷碗和這個大碗我一直在用。每一餐飯,我都會想起母親,這是她在給我特殊的愛。
作者:劉蘭根 編輯:李耀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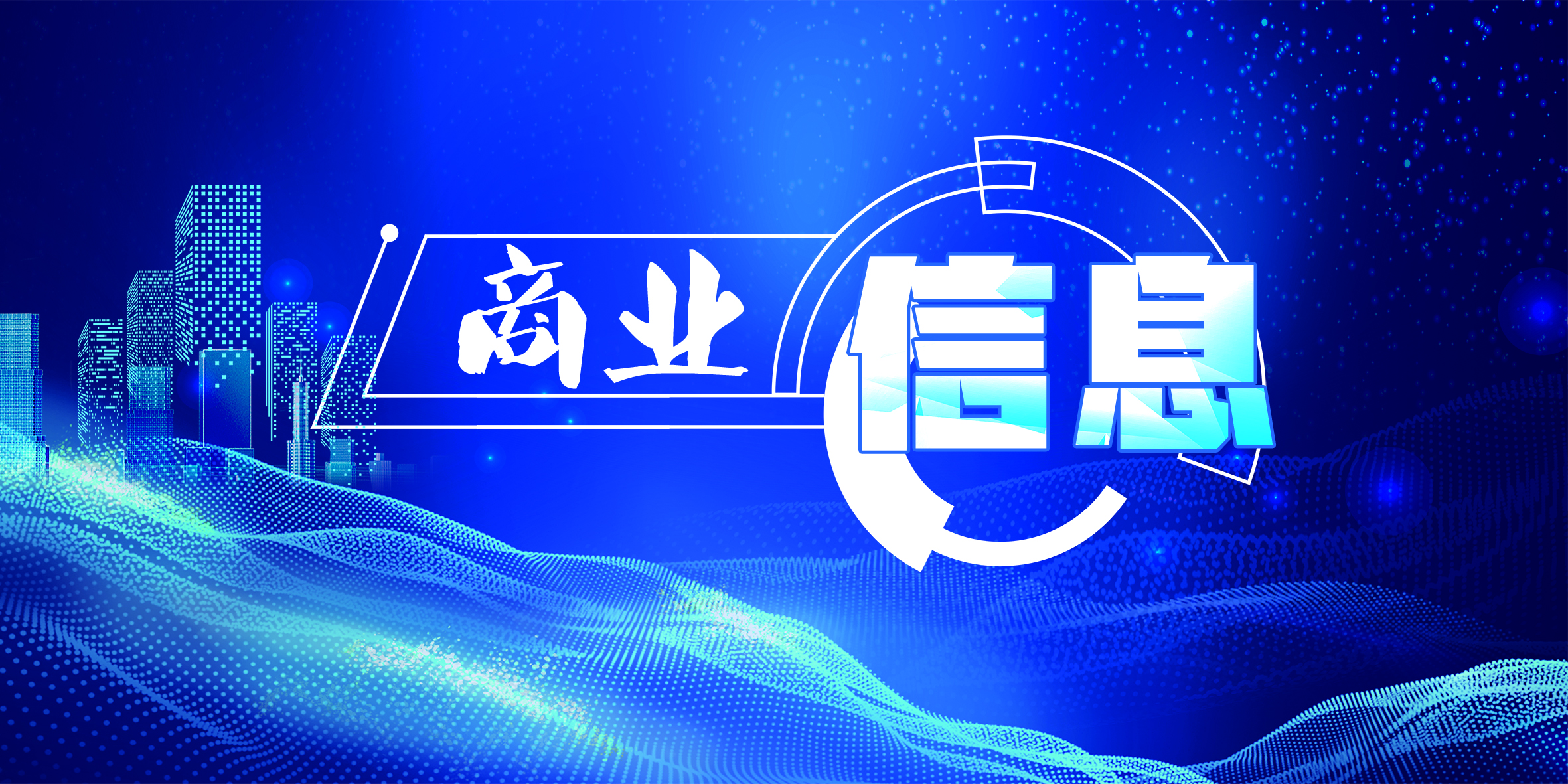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