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日子,在小區散步,一位鄰居正用木棍打砸地面上的豆秧子。我問:“自家種的?”他說:“不是,從北沼村的地里拾來的。”他還告訴我,現在收割豆子全是機械化,收得挺干凈。他和老伴拾了半天,才拾了這些。我看最多能落四五斤豆粒。看著這些豆粒,想起少年時期和我姨一塊去外村拾花生的情景。
我姥姥家在阜城縣李高村,我從小在那里長大,也在那里上學。李高村是黑土地,不能種花生。花生對于那時生活在黑土地上的農民來說,也是一種奢侈品。尤其是我們小孩子,更是吃稀罕,拿著當寶貝。逢年過節,家家都買幾斤炒熟的花生,預備著招待親戚朋友。我非常愛吃花生,喜歡那清香可口的味道。離李高村十來里地的漫河一帶,就是白沙土地,那里每年都大面積地種植花生。
我十歲那年的秋天,村里好多人去漫河一帶人家收完花生的地里拾花生。有一天,姨對我說:“小子,趕明兒你跟我一塊兒,咱上漫河拾花生去。”姥姥也在一旁進行“動員”:“跟你姨去,拾多少算多少。”當時,正趕上學校放秋假,小孩子沒事干,我很痛快地答應了。
第二天早晨,也不知是幾點鐘,反正天還漆黑,姨就把我叫醒。我們簡單地吃了早飯,帶上中午吃的窩窩頭。姨扛上一個扒鋤子和一條口袋,我拿著一個小镢頭和一個小布袋,和村里其他人一塊兒,成群結隊地向漫河走去。到了人家村的花生地里,天才剛剛發亮。
大家很快找到一塊剛收完花生的地,無需人指揮,就排起了長蛇陣,齊頭并進地開始刨土拾花生。大人們用扒鋤刨,幾乎是接二連三地能揀到花生,裝進口袋。我也緊忙活,小镢頭上下翻飛地刨著,但很少揀到花生。不大一會兒,我就腰酸腿疼,氣喘吁吁,只好干一會兒歇一會兒。一個大嬸看到后說:“不怕慢,就怕站,孩子,干呀。”我說:“腰疼。”大嬸說:“小孩子,沒有腰。”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中午,大伙兒就在地里吃點帶來的干糧,連口水也沒有。
下午五點來鐘,大家收工回村。到家一過秤,我姨拾了二十來斤,我那小口袋才剛夠五斤。大人們還鼓勵我:“行,拾得不少。”
出去十里地,到別的村去拾花生,這是我經歷的第一次。其實,拾麥、拾秋,對我們農村的孩子來說,是年年都有的事情。秋天拾秋,到地里扒拉著已掰完穗子的玉米秸,只要有玉米粒,大穗小穗都要。去豆子地里撿丟掉的豆棵子,運氣好時,可能會遇到豆子炸了捆的,落在地里的一片豆粒子。這時,就把小褂脫下來當包袱,把豆粒收起帶回家去。麥季,我們一幫小家伙相伴去拾麥子,湊夠一把,就用麥秸捆起來放到筐頭里。有時會碰見看青的(生產隊指定的看護莊稼的人)叔叔大爺。這時,有一個人一使眼神,大家心領神會,于是異口同聲,可著嗓門兒、帶著節奏地大喊起來:“拾麥,拾麥,連偷帶拽。拾秋拾秋,連偷帶丟。”這樣做的目的是跟看青的叔叔大爺開玩笑,想讓他們聽見著急生氣。誰知,看青的大人不僅不責怪我們,還笑瞇瞇得挺高興,直說:“這幫嘠小子,挺喜人的!”
拾麥、拾秋,我認為是一個好傳統。就如我們鄰居,進城這么多年了,還保留著農民勤勞、樸實的作風。把地里丟的糧食拾回來,首先是增加了個人的收成,其次是做到了顆粒歸倉,再是還鍛煉了身體。一舉三得,何樂而不為呢?
去漫河村里拾花生,過去了這么多年,我仍然記憶猶新,難以忘懷。
作者:費愛民 編輯:李耀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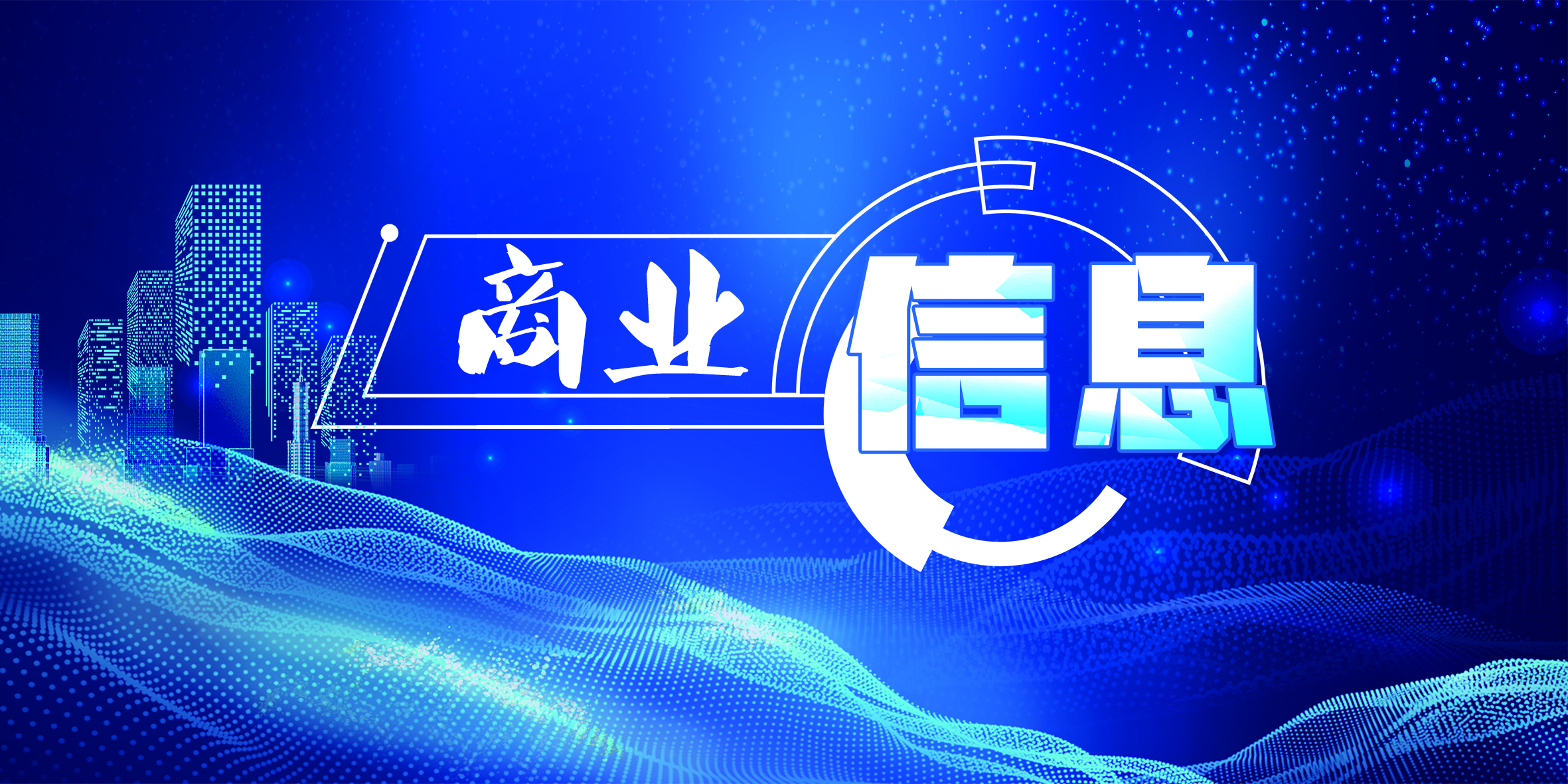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