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學要寫出普遍的、深刻的人性。
這是我一直秉持的觀點。我所有寫作都以此為綱。無論小說、散文還是詩歌,我用寫作發掘人性之良美,揭露人性之丑惡。早年間我讀到沈從文先生在《習作選集代序》中講到他以“供奉‘人性’”為主旨進行文學創作,慨然在書頁空白處寫下:任何人、任何團體出于任何需要編撰的文學史,都無法掩蓋您作品中散發出的人性的光輝!
鐵凝在一篇談論寫作的文章中提及:“偉大的文學應該是直逼人性的,而且應該具有對時代和社會的超越性的特征。好的文學要關注人類,關注人性的含量、審美和創造,好的文學也應該是人類思想最重要也最寶貴的活動之一,能夠代表作家所處時代對人性認知的最高水平。”
魯迅、索爾仁尼琴、川端康成、紀伯倫……文學的偉大之處,正在于關注人類,關注人性。
二
法國批評家埃斯卡皮為文學之門制定了一個門檻:“作家死后10年、20年或30年,總要到‘忘卻’那里去報到。如果某個作家跨越了這條可怕的門檻,他就踏進了文學入口的圈子,同時幾乎可能流芳百世……”
1942年9月8日,沈從文在他寫給大哥的一封長信中對自己的作品做了充滿自信的判斷。“我正想好好地來個新的十年工作計劃,每年來寫一兩本好書。我總若預感到我這工作,在另外一時,是不會為歷史所忽略遺忘的,我的作品,在百年內會對于中國文學運動有影響的,我的讀者,會從我作品中取得一點教育的。”
接下來,他以自己和某些人對比,自然講到了文學的功用。“眼看到并世許多人都受不住這個困難(前文提到日子窮苦寒酸)試驗,改了業,或把一支筆用到為三等政客捧場技術上,謀個一官半職,以為得計,惟有我尚能充滿驕傲,心懷宏愿與堅信,來從學習上討經驗,死緊捏住這支筆,且預備用這支筆來與流行風氣和歷史陳舊習慣、腐敗勢力作戰,雖對面是全個社會,我在儼然孤立中還能平平靜靜來從事我的事業。我倒很為我自己這點強韌氣概慰快滿意!”
我愿意預言,沈先生的作品定會跨越那條可怕的門檻,而同時代詬病、批判他的那些“高明”的作家們,也定會到“忘卻”之處去報到。
三
對于這道門檻,中國的文學評論家們直接選擇無視。作家李國文在一篇探討如何評價文學作品的文章中寫道:不知道什么原因,現如今,公允的評論越來越不多見,懷著私心,揣著私貨,泄著私憤,拿著私房錢的不公允評論卻越來越泛濫。當代文學評論家們最消極的一面,就是將文字當作“花露水”,遮掩所評作品的不足;將文章當作“雪花膏”,為一些并不值得推介的作品涂脂抹粉。
某女賦詩,不走尋常路,諸位大家力捧其獨樹一幟(竟有幾位是我原本較為喜愛的評論家,看到他們躋身其間,與有榮焉,目疼之極)。魯獎泛濫,鈔票選票互為交易,令嫉惡如仇的先生泉下結舌(某年去到紹興參觀魯迅故里,臨街迎面是先生擎煙沉思的畫墻。想到魯獎近些年的喧囂熱鬧,竟然還敢厚顏無恥地在先生注視之下搭臺頒獎,真想替先生大爆粗口)。此類事例稍一羅列,即可著一部《二十年目睹文壇之怪現狀》。
作家殘雪恰好在一篇《文壇跟黑幫團體差不多》的文章中給出了答案:“許多作家都在文壇混,同那些所謂批評家抱成一團來欺騙讀者。因為現在大多數讀者還不夠成熟,分不出作品的好壞。”殘雪一直被視為文壇另類,除了她作品的先鋒意味,還有她不吐不快的耿直秉性。文章最后,她破天荒地舉了幾個在文壇上將“混”稱之為“轉型”的名作家(太過有名,不便轉述于此),措辭頗為犀利,毫無情面可言。誠然,這僅為她的一家之言,可惜的是沒有一家報刊將不同的聲音釋放出來,供讀者自行評判。
熊培云在《月光中》有句:“人生痛苦之源不外乎兩種:一是惡揮之不去,二是美求之不得。”我借用一下,文學世界的苦痛莫不如是。
四
文學要為特定人群服務嗎?文學一旦喪失其獨立性,就毫無價值可言了。如果非要給出答案,我講,文學應為人民(整個人類)服務。一城一池,一門一派,一家一族,一朝一代,都不足以讓文學臣服。無論時間還是空間,文學若是主動從屬于某種局部利益,那它速朽的命運便早已注定。
夏堅勇教授在《大運河傳》中有一段事關文學的論述。以隋代為例,別有見地。抄錄如下。
“我們都知道隋代沒有文學,這固然與它立國時間太短有關,但最重要的還在于統治者對心靈的扼殺。”“知識界也彌漫著一股玩知喪志的實用主義風氣,文化人紛紛揮刀自宮,把心靈變成敲開利祿之門的石頭。他們寫詩作文是為了拍皇上的馬屁。歌功頌德,獻媚討好,成為當時文學藝術的主旋律。這種主旋律實際上是一種大棒加胡蘿卜的文化專制,作為政治專制的派生物,它當然也不會比政治專制寬厚和溫柔。它使一切有尊嚴的人賤賣自己去摧眉折腰,淪落為招招實惠的文壇阿混;它給所有的作品都強行抹上‘盛世’的油彩,在一片‘吾皇圣明’的頌歌中搔首弄姿發羊癇瘋。可以想見,這樣的作品怎么能散發出激情的血溫,怎么能燃燒起生命的光彩,又怎么能用來討論深刻和崇高?”
其實無論什么時代,都要以此為鑒。文學藝術尤甚。
五
依照我的閱讀經驗,作家大致可分為兩類:值得認識的與后悔認識的。
關于這個話題,錢鐘書先生有言在先。《圍城》一經出版,短時間內重印數次,還被譯成多國語言,受到世界各地讀者的追捧。有人鴻雁傳書,有人登門拜訪,先生不勝其擾,苦不堪言。某日接到越洋電話,一位英國女士求見甚急。錢先生天性幽默地回絕道:“假如你吃了一個雞蛋覺得不錯,又何必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誠然,先生的“母雞”一說并無褒貶。但仔細分析,其中又不乏“值得”與“后悔”的分別之意。先生淡泊名利,甘愿“板凳要坐十年冷”地做一門學問,厭煩了一切拋頭露面的事。殊不知,此一時彼一時,市面上總不乏那樣一群相當活躍的作家。
巴金在一封給他“粉絲”的回信中寫道:“對于作家,還是看他的文章有意思。我自己也有這個經驗,有時因為認識了這個人,連他的文章也不想讀了。自然偉大的作家不在此列。他們的生活與思想是一致的。不過我夠不上。因此我還是希望你讀我的文章。”
二位先生行事低調,說話委婉。再來看看那群市面上活躍的作家,總像一只下了蛋的母雞那樣“咯咯”叫著出現在一個又一個曝光的鏡頭里。上文中,沈先生評價這類人只用了四個字——以為得計。他們永遠不知道文學世界里有一條“忘卻的門檻”,這正是令我后悔與之相識的原因。
作者:賈九峰 編輯:李耀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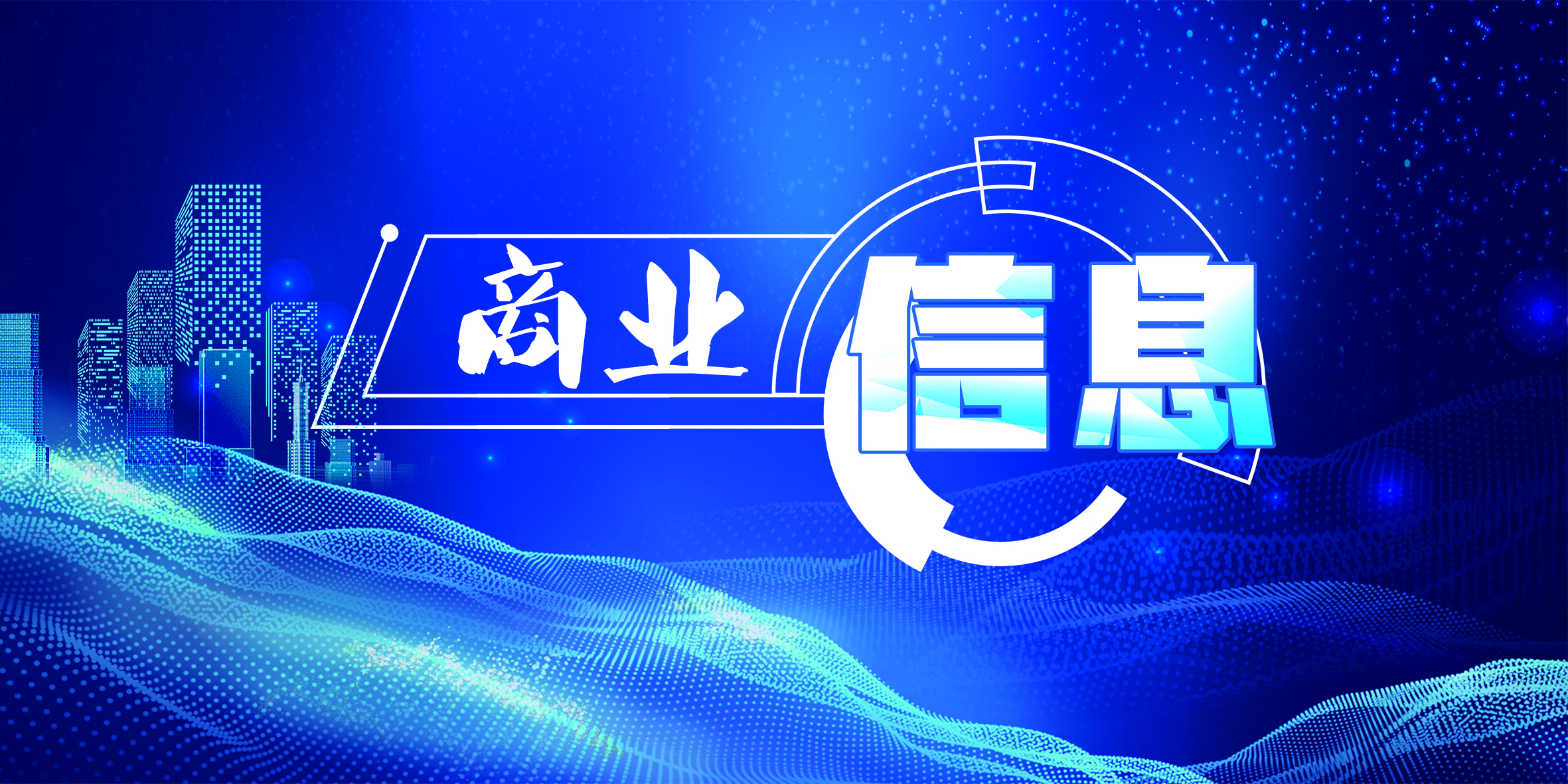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