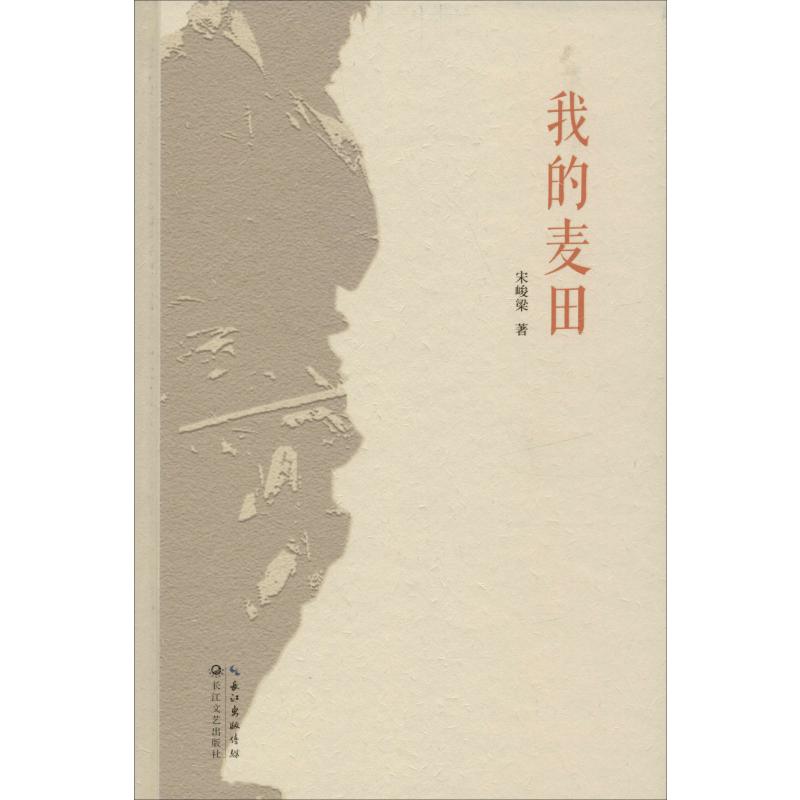
對鄉土的講述,我們的詩人和小說家都走過了遼遠而多歧的道路,他們曾經漂泊異域,用田園牧歌似的優美筆調贊美詠嘆鄉土的生活秩序、自然風光和被加工過的人情人世;也曾站在現代文明的立場上,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地批判那些前現代的落后和愚昧;還曾在思想意識的路上跑得更遠,鄉土只是他們安放作品的三腳架,在種種解構之后,他們用變形和夸張的形式,寫出藏匿在鄉間的暗黑和魔幻。宋峻梁顯然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要在這三者之間尋找更加適合當下時代和作者愿望的表達方式,他把鄉土與梵高、海子的詩意想象結合在一起,與個人的成長經歷和社會變遷緊緊相連。在他的筆下,鄉土并不是自維的,甚至也不是客觀的存在,它是被文學、藝術、歷史建構的存在,是自我的語境,個體在這里發現并辨認自我。
宋峻梁的詩集《我的麥田》盡管作者自稱是“獻給我的父親母親,獻給我的故鄉”,似乎是直指詩人的童年記憶或者鄉土書寫,但仔細閱讀后會發現,“我的麥田”雖然把鄉土作為了所指之一,卻早已超越了這種一般意義上的慣性指稱,而指向更多元,更含混的象征。要在梵高的《太陽下的麥田和人》《麥田上的鴉群》等作品與這部詩集之間建立聯系并不是一件牽強的事情,二者都在“麥田”的表層意象之上用色彩和語詞描繪了生命、力量,并試圖在有限的表現領域內探索個體與周遭世界的關系。另一個關于麥田的著名意象來自海子。《我的麥田》顯然有向海子致敬之意,第三章《村莊史》扉頁上就引了海子《熟了麥子》一詩:“有人背著糧食,夜里推門進來”。基于此,我們大可以把宋峻梁的“麥田”延伸向鄉土、歷史乃至人類文明發端之處。
詩集一共六章,首尾相連,貫通一氣,敘事性與抒情性、思辨性兼顧,既是“我”外出、游蕩、返回的個人史,也是人與鄉土,與歷史在不斷講述中重建聯系的發現史。詩人在傳統史詩所慣用的游歷、尋找母題中注入了更多思考和詰問,將傳統史詩的講述故事轉向講述自我,在漫長的尋找中完成對自我的講述和發現。第一章《游蕩者》為全書的敘述帶入了一位在城鄉間“游蕩”的主人公“我”,他將成為全書在幕前活動的最重要角色,成為觀察、感知、講述的主體,為詩人代言。關于“游蕩者”的命名很容易令人聯想到現代派詩歌中的“流亡者”形象,但與“流亡者”將流亡作為反抗確定性和意義感的存在方式不同,宋峻梁的“游蕩者”顯然已經走過了那種決絕而輕率的否定,他說:“我沒有迷失/我保存各種可能和懷疑/我一直走在路上”。
我們隨著“游蕩者”,走在人生所有可能的地方。他在田野,看“村莊很遠又很近”;他回到南方的租住地,“在大片的廢墟邊徘徊”;他“曾坐在山頂/俯視下面的萬家燈火”,“也曾在大海邊聽著潮聲入睡”;他“騎著駱駝奔跑過荒廢的都城”把“曾經生活的城市的方向”作為“那一刻我奔跑的方向”。為什么要這樣游蕩呢?詩人既無意在浪漫主義美麗的大旗下尋找遠方,也沒有致力于在游蕩的過程中驗證現代主義或者后現代主義的虛無頹廢,他說:“我想反復確認這個世界/每個地方都與我有關。”毫無疑問,這句話非常關鍵。這既是“游蕩者”的自白,也是詩人有意點出的全書主旨。在游歷中尋找自我,在講述中確認自我,在歷史中重建當下。
敘述從《游蕩者》開始,當“我在土地里翻身醒來”,第二部分《影子》開始了。《影子》宣告了“我”在城鄉間游蕩的結束,這一部分的表述空間被基本限定在村莊外圍。“我”在這里觀察、窺視著村莊和附屬于村莊的土地、動物、植物,最重要的是“我”在這里發現了另一個“自我”:“你是神么/是什么神/三頭六臂/火眼金睛/或者只是一只猴子/只是渾身塵土的風/掛在樹上不下來”。“他”亦即影子,回答說:“我是你啊/傻大個”。宋峻梁用了很長的篇幅來講述“我”與“影子”的對話,在對話中不難看出,“我”對以“影子”角色出現的另一個自我充滿了懷疑、諷刺、不屑;而“影子”則毫無芥蒂地致力于緩解“我”與環境的齟齬。影子說:“在你入睡后/我星夜趕路/到你曾經去過的地方/見你曾經見過的人們/幫你向每個你辜負的人道歉/向每個幫過你的人道謝/也許我會請他們喝杯小酒/我會掏一元紙幣/給過街天橋上/殘疾的乞丐/你曾經視而不見/硬著心腸走開/我也會走進你痛恨的/曾經帶給你屈辱的人的夢里/替你打他一巴掌/讓他忽然醒悟你的善良”。顯然這是自我一體兩面的分裂與對話,二者之間的互否令人不安卻并不違和。
第五章《我的麥田》無疑是全書最華彩的部分。詩劇的形式為本節帶來最多樣的表現手段和最豐富的表達內容。眾多人物被詩人召喚到“麥田”,在這里上演了一幕幕充滿自白和詰問的活劇。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歌德的大型詩劇《浮士德》,盡管從體量上來說二者并沒有可比性,但詩人向前輩致敬之意還是有跡可循的。詩劇共分六幕,以“賊”的闖入始,以關于“稻草人”的旁白終。稻草人是最熟悉麥田的人,卻并不是麥田的擁有者,農夫農婦才是,他說:“我自己已經成了/一座正在發芽的十字架/或腐朽的十字架/成了麥田里最高的墓地/只不過誰也不會感到害怕/也不會對我肅然起敬”。在第二幕中,他為賊講述自己,“城市里我生活過,愛過/甚至死亡過/大街上眾人如一/沒有人知道我是誰”;第三幕中,他引賊去看那些“夜間的事物”,“我看到一群人正從麥田起身/借著月光/擦拭身上的液體……”那里,有盜墓人、有鬼魂們、有死去的國王、有財神、有判官。稻草人和賊的對話在第二幕中還主要是對自我的講述和懷疑,到了第三幕,他們的詰問和懷疑擴展到了神的存在。賊在追問:“神在哪里?我從未見過/誰是神/你是否能一一指認”?稻草人的回答并不像回答,他說:“未來的孩子們……他們一出生/便介于神與人之間”;說:“那些早早被封為神的人/一直沒有被推翻過……我知道他并不太信這一套/只是做做樣子騙一下”。實際上,詩人在這里談到的神并不明晰,是指代來自印度或者西方的宗教信仰,還是中國民間的鬼神崇拜?但不管怎樣,在稻草人和賊的對話中神被調侃,被懷疑,被一一解構,神并不能為人帶來精神皈依,甚至不能使他們感到平靜安全。正如宋峻梁在《后記》中說:“是前往神的寓所,還是還鄉?人的精神皈依問題是個大問題。《我的麥田》選擇了后者。”
第四幕的《小舞臺》算得上劇中劇,無論是唱歌的女學生們、還是拍照的新婚夫婦,都在向我們展示生活美好、熱情、充滿陽光的一面。自從“希望”最后一個被從潘多拉盒子中釋放出來,它就支撐起了人類面對未知的勇氣。詩人也許是借著青春少女和處在最大幸福中的新娘來表達他對世界的美的贊賞和愛意,但他甚至不能讓這種贊賞保持到這一幕結束,“一個滿臉污垢的女子闖進麥田,頭上插滿鮮艷的花朵”。大概就像魯迅在《藥》的末尾,給夏瑜墳上添一個花環,是要在一片晦暗中增加一些希望和亮色;詩人讓瘋女人闖入,正是在一片光明美好中添一些絕望和凄厲,讓所有的肯定中生長出否定的元素。
第六幕麥田復歸寧靜,但這寧靜里有喧囂之后的荒涼沉寂。稻草人的自我束縛和賊的不斷逃離儼然是人類的一體兩面,他們不斷懷疑,不斷詰問,在現實面前潰不成軍,卻又強大無比地始終不肯放棄思考:“這里不是你的/也不再是我的/空空蕩蕩的大地上游蕩的全是/未曾安息的靈魂/我愛過的依然會愛/恨過的依然會恨/烙印就像皺紋一樣堆積在我心里/無法改變的事情太多了/這騷動而又寂靜的大地/仿佛絕境/仿佛一只巨大的手掌/這就是我的故鄉/這片土地也曾經是祖先們的廢墟/然而我無法拍打家門/我回來了,可是我想住在麥殼里/蟲洞里,我想住在/我自己的身體里/這些草這些花枝這些破布/我也厭了/麥田是我的懷抱,忽然消失/土地是我的墻,它橫亙在那里/趁著夜色,我們離開吧/去哪里不重要。”當稻草人有了離開的念頭時,賊說:“我要做你的背影,你在這里/我就在這里/做你的另一面/我克服了懼怕/但我還沒有克服孤獨。”他們的表演結束了。麥田曾經容納了人類一切的歷史和現實,悲哀和快樂,也必將繼續容納人類的未來。人類一直不斷地從麥田出發又回到麥田死去,卻從來不肯安靜地待在原地。他們不能停止流浪,不能停止探索,他們既是麥田的稻草人又是被追索的賊,麥田束縛他們又包容他們,他們只有在跟自己和麥田的對話中才能真正找回自己。
于是,就有全書終篇《我在》。在這里,所有人和物都成過眼云煙,只有村莊和“我”依然:“村莊的中間是一條道路/一個方向通往城市/另一個方向通往沒有墓碑的墳場”;而我:“我在同所有陸續到來的和曾經相遇的事物妥協”“作為一個消失過的人/我在重新嫁接生活”。
現代社會發展到今天,個體的現代性焦慮已經成為一個普遍問題。人成為了“原子化”的自我,在宇宙人生中煢煢孑立,只能活在當下,對歷史與未來都充滿了茫然之感。與之相伴的是新時期以來文學對“人”的重新發現逐漸演變成對“自我”的過度迷戀,現實中的自我中心主義與詩歌中的私人化敘事相呼應,詩歌成為表現自我的手段,自我迷失在詩歌語言的迷宮中。我們一直在追問,我是誰?《我的麥田》雖然有部分“村莊史”的屬性,但歸根結底還是一部關于“自我”的游歷和發現史。麥金太爾提出了“敘事性的自我”的概念,他認為,一個人的人格構成表現為這個人一生中首尾一貫、意義明確的各種活動及其敘事,這是在特定的歷史傳統中或社會脈絡當中展開的,個人的生命意義感的形成也是與這種歷史和社會密不可分。每個人都是有故事的自我。《我的麥田》完美演繹了麥金太爾“敘事性的自我”的論述,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表達方式,一種把鄉土和所有經歷作為個體記憶和存在方式的親切的表達。
作者:吳媛 編輯:李耀榮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