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
朝廷給滕的罰單是慶歷四年的正月初四開出的。“降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權(quán)知鳳關(guān)翔府滕宗諒為祠部員外郎、知虢州,職如故。”除了首當其沖的“降”字略表懲治之意,罰單通篇沒看到實質(zhì)性的處罰。御史臺的諫官們大為不滿,以集體“罷工”表示強烈抗議,居家待罪,繼續(xù)給皇帝施加壓力。
其實對于滕的調(diào)查早在慶歷三年初夏其移任慶州之初就已經(jīng)開始了。事情起因也簡單明晰——十六萬公使錢。盡管不是小數(shù)目(以購買力折合人民幣約兩到三億),但到底還只是經(jīng)濟問題。圍繞此事角力的雙方其一為新政精英集團,另一方為舊的政治利益集團。誰都明白,一旦與政治攪和到一起,事情就變得復雜難纏了。
慶歷新政以范仲淹、富弼聯(lián)署上書《答手詔條陳十事》為標志,是仁宗親政之后著手實施的一項穩(wěn)妥至上、態(tài)度溫和的政治改良。既便如此,那些既得利益者依舊對新政恨之入骨,百般阻撓。滕宗諒與范仲淹出身同年進士,志同道合,貴為密友,一向是新政的堅決擁護者,在其所轄地方積極推行,勇于落實,干事任能,廣交文友,得以詩文播布京師,成為新政樹在中央的一面旗幟。此次對滕的彈劾奏章一出,舊勢力豈肯輕易放手,恨不得給諸位新政精英扣上一頂“朋黨”的帽子,一棍子打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
五千年的政治斗爭史告訴我們,若要置對方于死地,“朋黨”二字最具殺傷力。宋家天下靠兵變上位,重文抑武同時,一樣擔心文人互結(jié)營壘,與皇家離心離德,自行其是。正是在如此嚴峻惡劣的形勢之下,范仲淹不避嫌疑,挺身而出,他主張派人前往涇州和慶州調(diào)取“錢帛文帳磨勘”,逐一審計。如果查出滕有貪污問題,他甘愿與之“同行貶黜”。
滕子京并非貪財之人,但他好大喜功,手面闊綽,干事成事,愛講排場。一批批文人墨客浩浩蕩蕩地應邀來到?jīng)苤荩轿骶€邊陲采風寫作,管吃管住管旅游,臨走再封送一個大紅包,隨著詩文流播海內(nèi),滕也聲名日隆。公務宣傳與個人包裝本來就難以區(qū)分,再加上仁宗礙于范仲淹“橫身相救”的情分不便深究,遂開出了上面那一道和稀泥似的罰單,招致了御史臺諫官們的集體抵制。仁宗之“仁”,一半得益于他的和泥功夫,那就再安撫一下諫官們的情緒吧。于是二月十四日,在罰單空白處增添一句:徙知虢州滕宗諒知岳州。如此這般,滕子京來到巴陵,新官新政新氣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時已至此,岳陽樓呼之欲出!
百廢具興。可見滕在岳州任上做事頗多,但其他的事都已在歷史上湮沒無憑,只留傳一件卻讓他名垂青史——重修岳陽樓并請范仲淹作記(有此一事,足矣)。推究岳陽樓歷史,應始建于三國東吳時期,魯肅為湖上操練水軍在巴陵山上修筑閱兵臺。唐開元名相張說因執(zhí)言獲貶,謫守岳陽擴建閱兵樓,正式定名岳陽樓。慶歷五年,重修岳陽樓工程已近尾聲,撰寫《岳陽樓記》一事提上日程。在古代,“記”文大都由主人親自執(zhí)筆,以便抒發(fā)胸臆,賦予“記”更為深遠的意義。滕子京身為地方長官,又有進士學歷,完成這樣一篇“記”文應該不難。但他心目中卻有更為合適的人選,或者說有人比他更符合為岳陽樓作記的條件。其條件有三:名人、文人、友人。同時滿足上述條件者非范仲淹莫屬。于是他開始給范寫信:“天下郡國,非有山水環(huán)異者不為勝,山水非有樓觀登覽者不為顯,樓觀非有文字標記者不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君文章器業(yè),凜凜然為天下之時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信寄出了,那么范仲淹為《岳陽樓記》做好準備了嗎?
最近一年,仁宗在新舊勢力之間左右搖擺,依違兩端。又加舊勢力處處阻撓,令新政推行舉步維艱,幾乎成了“爛尾工程”。仁宗失卻耐心,毀謗隨機跟進。范仲淹失望之余,自請出知邠州,巡邊西北,遠離了政治中心。慶歷五年秋冬之際,在歐陽修貶知滁州的同時,他上書朝廷,請求調(diào)離邠州,退居閑職。朝廷成全了他的心意,派他改知鄧州。“數(shù)年風土塞門行,說著江山意暫清。求取罷兵南國去,滿樓蒼翠是平生。”宦海浮沉,人事遷變,歸途在即,他的人生觀、價值觀、榮辱觀、政績觀、文學觀已然煅造得宏闊、厚重而純熟,是時候形諸文字、流傳天下后世了。由此看,范仲淹著《岳陽樓記》,既是滕子京的選擇,更是歷史的選擇。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如果早一天,范仲淹可能寫不出這樣一段文字。如果晚一天,范仲淹可能會將這段文字埋藏心底。無論早晚,我們都無法讀到震古爍今、光芒萬丈的《岳陽樓記》。“在十一世紀蒼茫夜色下,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精神面貌演變進程中,一顆新的太陽升起來了,那是一種把‘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寫在旗幟上的光風霽月般的人格境界和精神風范。”因為這一面飄揚的旗幟,在江南三大名樓中,雖然岳陽樓的資歷最淺,卻因其高標獨立的精神文化意義,影響著一個民族的心靈史,這種影響必將會無限持續(xù)下去。
文章最后旁涉兩件史事。一是南宋紹興二十五年六月,左朝散郎姚岳上書朝廷,因恥與岳飛同列,并全力消除岳飛的影響,申請將岳州改名純州,以體其忠純報國之心。污名岳飛,自然暗合丞相秦長腳的心意,大筆圈定,岳州改純州,岳陽樓隨之更名純陽樓。半年不到秦檜病逝,但是令岳陽樓蒙羞的這段歷史卻持續(xù)了六年之久,直到紹興三十一年改回。二是明代洪武初年,蘇州人范從文因違背皇帝旨意而判處死刑。行刑前,朱元璋親自查看案卷,看到范的姓名和籍貫,便傳喚至跟前問:“你不會是范仲淹的后人吧?”范答:“我是范仲淹的十二世孫。”朱元璋命人取來錦帛,御筆寫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賜給范從文,并下旨“免除五次死罪。”人命關(guān)天,朱以皇帝之尊,方才贏得片刻景仰范仲淹的資格。
“噫,微斯人,吾誰與歸!”《岳陽樓記》最后發(fā)抒的這一聲千年浩嘆,常常令我聯(lián)想起魯迅的話:“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看到蒼茫大地的深處,一個個孤獨寂寥的身影,決絕而默然前行。我愿意加入進去,踩著他們的腳印,在荒野里踏出一條憂國憂民的長路。
作者:賈九峰 編輯:李耀榮








 廣告
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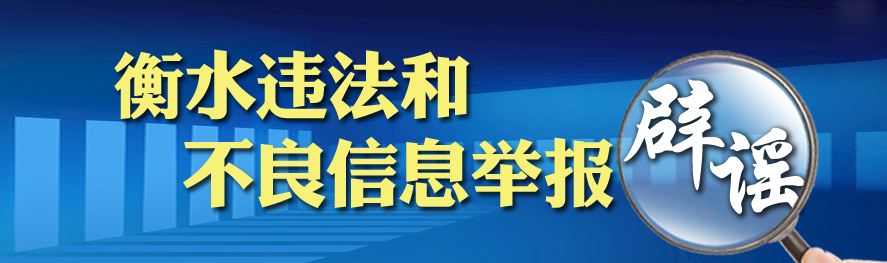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