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云天,黃花地,西風(fēng)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詩詞的力量不容易被發(fā)現(xiàn)。一部詞曲俱佳、美輪美奐的《西廂記》,不僅讓普救寺史上留名,還將四大皆空的佛門凈地演繹成為老百姓心目中的愛情主題公園。
峨嵋塬頭高達(dá)三十米,腳下是一條自東而西、直達(dá)蒲津古渡的馬路。正是因?yàn)轳R路的關(guān)系,如今游人們無法從山門進(jìn)入普救寺前的廣場,只能在小鎮(zhèn)的街口下車,沿著一排商販攤位喧囂而過。正面的山門反倒只可從背面約略參觀,再回轉(zhuǎn)身來細(xì)細(xì)端詳刻有“普救寺”大字的歇山飛檐式照壁。照壁之后,廣場中央立著一把涂金的同心大鎖,鎖上毫無避諱地直書“愿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天下寺院不談情,唯有山西普救寺。毋須進(jìn)門,僅此一語就道明了偉大的愛情主題。
根據(jù)出土文物考證,普救寺或初建于南北朝末年,名西永清院。隋唐兩代多有修葺。至五代后漢時,河?xùn)|節(jié)度使叛亂,郭威領(lǐng)兵征討,圍蒲州城而久攻不克。寺中問計(jì),僧人直言:善待百姓,城池可下。郭威折箭為誓,果然攻破州城。有誓為先,城中百姓得以保全。因此禪院更名普救寺。普救寺得名的由來,坊間大都采信此說。值得一問的是,《鶯鶯傳》原文中已寫有普救寺名,而此篇傳奇作者元稹生活于唐大歷至太和年間,與后漢政權(quán)建立前后相差近一百五十年。這又如何解釋?《鶯鶯傳》最早見于宋太平興國三年成書的《太平廣記》,難道有宋人因普救寺名而篡改原文?此說顯然缺乏說服力。經(jīng)查,《太平廣記》收錄《鶯鶯傳》一文轉(zhuǎn)自唐末陳翰編著的《異聞集》,故事原題《傳奇》。既然是唐末成書,其地名差訛當(dāng)不復(fù)存在。可唐末原著《異聞集》已佚,宋代所見《異聞集》一書中,偏又混入了宋人故事,其可信程度已嚴(yán)重降低。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一書中指出:“《鶯鶯傳》為微之(元稹)自敘之作,其所謂張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無可疑。”顯然他的考證重點(diǎn)不在普救寺名稱的由來,這是不是也從側(cè)面說明普救寺名出現(xiàn)在元稹的筆下已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了呢?
入得寺門,小行片刻,便依塬而上,第一個平臺即到“勾心斗角”、氣勢雄偉的大鐘樓。從此地開始,我們每到一處,都可與《西廂記》彼此對應(yīng)。比如這座大鐘樓,正是《西廂記》“白馬解圍”一折中的觀陣臺。張生為解普救寺之圍,特搬來好友白馬將軍救急。兩軍交戰(zhàn)之時,張生邀請老夫人和法本長老等僧眾共登大鐘樓觀戰(zhàn)助威,為大破敵陣生擒孫飛虎齊聲喝彩。
經(jīng)過塔院回廊,攀登中一昂首,眼前一座高塔直插云天。在我舊有的印象中,佛塔總是出現(xiàn)在寺院的最后方(因?yàn)楣┓钪鹱嫔崂辽僖ㄔ诖笮蹖毜钪蟆A碛幸慌f識——只有建有大雄寶殿的寺院方可筑塔,此說忘了出處,又一時無從查考,先行記在這里,待專業(yè)人士指正。此塔建于塬頂最高處,更是建在大雄寶殿之前,令我破除陳規(guī)。該塔初名舍利塔,后因《西廂記》名聲大躁,只得依照世人俗稱鶯鶯塔。夕照昏黃,鍍塔成金。塔尖之上,有一群暮歸的烏鵲盤桓回旋,晚風(fēng)中時起時落,短啼長鳴。“鷓鴣聲聲不堪聞,鶯鶯塔前月影深。西廂院外有情癡,一本傳奇唱到今。”居高臨下、俯察一切的寶塔想必也見證了張君瑞與崔鶯鶯的愛欲交結(jié)與悲歡離合吧。
鶯鶯塔的奇妙之處在其匪夷所思的回聲效果。據(jù)傳在塔周圍十五米左右的距離內(nèi)拍手或擊石,就能聽到從塔底傳來清脆悅耳的蛙鳴聲。如果再退后五米,蛙鳴聲又自塔頂傳來,仿佛金蟾忽上忽下,與人嬉戲。若是在夜深人靜之時,扣石一聲,神蛙三鳴,且來自三個不同的方向。鶯鶯塔與天壇回音壁、三門峽寶輪寺塔、潼南大佛寺的石磴琴聲并稱為中國古園林中四大回音建筑。我佇立塔下,任三兩游人擊掌或扣石,咯哇咯哇,果然靈驗(yàn)。
香煙繚繞之中,我從眾多善男信女跪拜的身后走過大雄寶殿,徑直奔向大殿東側(cè)的梨花深院。如果不是耳畔時有誦經(jīng)聲隱約拂過,站在小院天井里,真會疑心是闖入了某一富貴縉紳的私宅。宅門楹聯(lián)是晏殊小詞《無題》中的一聯(lián):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fēng)。細(xì)細(xì)品味,有市井氣,有脂粉氣,有七分雅靜,又有三分曖昧,這副對聯(lián)恐怕也是天下寺廟絕無僅有的吧。精致的小院完全依照《西廂記》中的描寫建造,任何細(xì)節(jié)都做足了功課。在東廂房南側(cè)的粉墻之下,一叢翠竹環(huán)抱著玲瓏湖石,正可做逾墻人的墊腳。墻外是一株高矮恰好的杏樹,如此一里一外,共同成就了戲文中的千古絕唱:“待月西廂下,迎風(fēng)戶半開。隔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安立在西廂南側(cè)的出土文物“金代詩偈”,詩名刻“普救寺鶯鶯故居”,跋文載詩作于金代大定年間,最為直接地證實(shí)了崔張故事在宋金時就已廣為流傳。“無據(jù)塞鴻沉信息,為誰紅燕自歸來。”從頷聯(lián)所傳達(dá)的詩意可知,崔張的愛情結(jié)局并非如戲中所唱那般圓滿。
擁有原創(chuàng)版權(quán)的元稹的確不是憐香惜玉之人。《鶯鶯傳》的真實(shí)結(jié)尾是“文戰(zhàn)不勝,張遂止于京。”始亂終棄的張生最后以衛(wèi)道士的口吻四處宣告:“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何其冠冕堂皇!何其大言不慚!這簡直是要置鶯鶯于死地!陳寅恪先生篤定張生即是元稹,想來早已看穿了元才子的薄幸本質(zhì)。如果有人以鶯鶯是虛構(gòu)人物為之辯白,那么投河自盡的劉采春不正是現(xiàn)實(shí)版的崔鶯鶯嗎?劉采春年輕貌美,歌藝俱佳,在唐朝歌壇獨(dú)樹一幟,罕有其匹。越州刺史元稹一見心動,舊病復(fù)萌。先是搖筆贈詩,博取芳心,后又動用官場資源,付給對方丈夫一筆銀子,買斷了劉的婚姻。但等消費(fèi)完畢,保鮮期一過,便又重拾張生伎倆,打起了道德太極。劉采春留有《啰唝曲》六首,首首都是對負(fù)心男人含淚泣血的控訴。其一曰:“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婿去,經(jīng)歲又經(jīng)年。”可憐無名無分、不清不白的劉采春只得攜著一腔癡情赴水東逝。
小院后身,緣階而下,是玲瓏周至的后花園。水榭風(fēng)池,曲橋花亭,全部是依文附會,意思而已。作為歷史悠久的十方禪院,普救寺東區(qū)還建有天王殿、菩薩洞、羅漢堂和藏經(jīng)閣等眾多建筑,但這里游人稀落,古殿沉默,分明都做了待月西廂的陪襯。出得寺門,回首仰望,一輪明月高高升起在峨嵋塬頭,朗照著長長的蒲坂和雄渾壯闊的黃河水。日月無私,亙古照明。普救眾生,非無私無以脫離苦海。同樣,愛情的高尚之處亦不在相互占有,而在這“無私”二字。
作者:賈九峰 編輯:李耀榮
 廣告
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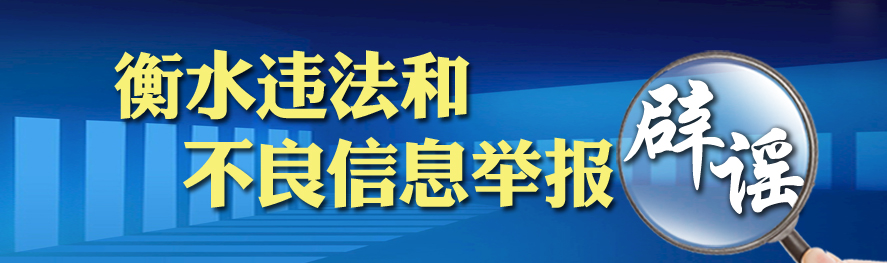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