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薇山下客,系馬夕陽斜。半醉尋歸路,花深不認家。”在眾多吟詠冀州的詩篇中,獨愛這首清新雋永的五言絕句——《紫薇山》。
詩作者石九奏,字伯成,號四如。冀州堤北橋村人,明萬歷二十年進士,官至正三品。舊志載,石九奏“工詩、古文、詞,好鐘書,淋漓揮瀝,動輒數百紙”,確是一位“文能提筆安天下,武能上馬定乾坤”的能才賢士。
辭官后的石九奏葉落歸根,于信都城西北筑“半園”而居,“蒔花種菜”,詩文唱和。《紫薇山》應為此時所作。
先生為何對紫薇山情有獨鐘?這就要從此山的來歷說起。紫薇山名“山”而非“山”,其實是信都城東北二十里處一座高達數丈的土阜,但傳說為大禹或他的父親鯀治水時用來擋水的大堤,這一說法,為這個本不起眼的丘阜籠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更為神奇的是,紫薇山有一盛景,位列明代“冀州八景”之首,名為“紫薇夕照”。諸多舊志均有載:“高數丈,旁多膏腴,桑柳連蔭,尤宜晚眺”,“此山每當初旭微霞,或水云相映,直上隱隱有樓閣人物之狀,居民相傳為竹林寺”,明進士冀州謝瑞,修撰趙州劉世盛等等皆有歌詠紫薇山的佳作,一時之間成為文人墨客爭相到訪之地。四如先生之“半園”恰在紫薇山下,“蓋州北紫薇山隆隆丘阜,隱花園后作元武”(明王相極《半園記》),由此可見,先生與紫薇山便頗有些“相看兩不厭”的味道了。
作者戲稱自己為“紫薇山下客”,“客”在古人的詩詞中,多為“旅居、客居”的意思,頗具漂泊孤獨之感。如王維的“獨在異鄉為異客”,王灣的“客路青山外”,先生本就是冀州人,為什么也以“客”自稱?我推斷,一是因為作者宦游他鄉,離家多年,今夕辭官還鄉,猶如“游子”重回故鄉的懷抱,內心難免油然而生物是人非之感,對于故鄉而言,他儼然已經是“客”了。再者,對于自然界中的美景和一切美的事物而言,所有到訪之人誰不是“客”?我們流連其中,盡攬其美,賦詩吟詠,但誰也無法真正去擁有、占有,你來,或者不來,山就在那里。正是出于對自然的敬重,對其中之意的深刻理解,作者才自稱為“客”。以山水為樂,卻又超脫于山水之外,似客而非客,這其中傳遞出的,恰是作者深邃的哲思和超脫的情懷。
古人常以酒入詩,詩與酒是文人墨客筆下分不開的伴侶。詩人與朋友相攜,結伴而游,春風十里,陌上花開,于亭榭之上,或樓閣之中,與清風為伴,與美景為朋,煮酒論詩,酒微醺,人半醉,方覺夕陽西下,暮色漸沉,應是歸家之時了。但目之所及,卻只見晚霞之間,湖水微瀾,漁歌歸棹,山上的野花,岸邊的繁花,還有湖里的荷花,粉的,紅的,紫的,那花的香氣中,還纏繞著梵音暮鼓,交雜著古寺城垣。這一派盛景之中,恍然若失,酒不醉人人自醉,哪里還找的到歸家之路?讀此句,令人不由聯想起易安居士的名句“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這一“醉”一“歸”之間,折射出的恰是“得之心而寓之酒”的山水之樂,是先生內心縈繞半生的“浮云游子意”。
今日,也常于閑暇之時漫步于衡湖之濱,撫今追昔,更覺冀州之美美得醇厚,美得深遠。她有故事,有歷史深處綿延而來的幽遠和滄桑,她也有活力,有新的時代賦予的蓬勃的生長力。半生居此小城,她的一草一木,一顰一笑,已經深植于我的血脈,浸潤了我的所有。故鄉,是藏在心底最深處的一壇佳釀,即使你漂泊萬里,她始終在你的心里不停地發酵,只待你不經意間地觸碰,便會酒香四溢,醉了一生。
或許,這正是彼時四如先生所感吧。
作者:張紅霞 編輯:李耀榮
 廣告
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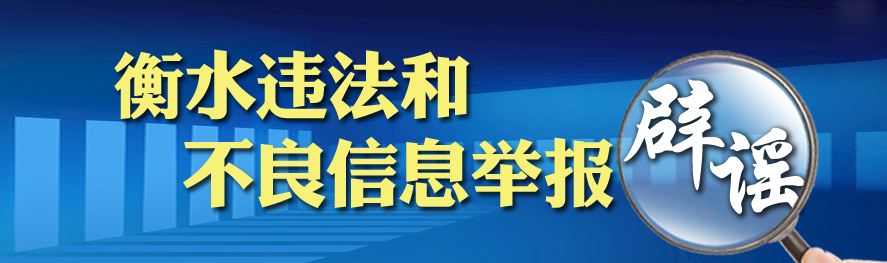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