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是個小偷,他先把熱鬧的秋天偷了去,那些蟈蟈兒、喇蛄、蛐蛐誰也不唱歌了。接著又把我家院里那幾棵棗樹、榆樹的衣服也偷了去,害得我連做飯都少了菜。更可氣的是他把我老姥爺也偷走了。
至今我還清晰地記得那是個怎樣的午后。太陽明晃晃的,整個西沿灣村都在光里打著盹。我扒開老黃狗的眼皮,一松手它就又合上,眼里滿是嫌惡。母雞們擠在刨松散的土坑里縮著脖,大公豬曬著肚皮流著涎水打呼嚕。我拿著一截小樹枝,對著一個銹鐵皮罐子,東敲一下,西敲一下,其實它的嘭嘭聲一點也不好聽,可這總比沒有聲音強些吧。
“咦?誰的腳步聲?小跑著奔我們家來了?”
“嬸子——呀,忙——著吧——俺爺爺——不行了……”
還沒進門,大妗子拉著哭腔的長音便先擠了進來。睡眼蓬頭的姥姥一邊胡嚕著頭發(fā)一邊踉蹌了出來,在成功地踢翻了我的破罐子后,她就緊倒騰著一雙小腳跟大妗子走了,臨走那群沒眼色的雞也挨了兩腳。
“姥姥,我哩,誰看著我?”回答我的是長久的寂靜。
我大妗子口中的爺爺,是我姥姥的公公,我是明白的,我管他叫老姥爺。
“老姥爺不行了?他怎么會不行了?”
這個問題對一個六歲的孩子有些高深。因為在我眼里,他一直是很行的。比如他領(lǐng)我去地里砍草,哪種草都是他的“熟人”,不像我姥姥,就認識那么幾樣。
“這個開紅花的是地黃,你嘬它的花蜜,我挖它那根。”
“長刺的青青菜也是藥材,喂豬、喂雞都行嘍,它愛欺負人,你得使勁兒攥它,越不敢拿,它越扎你。”
“青青菜,遍地發(fā)。越使勁,越不扎……”老姥爺一邊砍草,一邊哼起自編的調(diào)調(diào),那古里古怪的哼唱,常使我發(fā)笑。
“這藥寶可是個好東西,別看它長得像個蘑菇。蘑菇蓋子薄,不跟它肉多,等它張了嘴,里頭的黃藥面能止血,剌破嘍按上點就不流血了。”
他嘮嘮叨叨地說著,我一個耳朵聽著,一個耳朵冒著,心思早被地頭那片野葡萄拽了去。他看著我還蓋不住小籃子底的幾棵草,摘下草帽使勁呼噠幾下,好像草帽很生氣,又噘噘山羊胡子哼一聲,才收了我的鐮。
“光知道玩,長大了人誰家待見個懶閨女呦,去吧,別跑忒遠嘍。”
我歡呼著奔去,螞蚱們也跟著我一起蹦跶著。
“螞蚱,螞蚱,你這么高興,是不是也知道一會兒跟老姥爺回去,姥姥又該夸我有材料了。”
“哦,你不興告訴別人,草不是我砍的。”
這么有能耐的人,怎么就不行了?他不行,誰還行呀?我想不出來。
陽光依舊晃眼,風(fēng)悄悄來過,只落在扁豆蔓上蕩了幾下秋千就又走了。最愛湊熱鬧的大家佬兒(麻雀)哩,跑到誰家樹上去了?發(fā)了一會兒愣,我拾回那個破鐵罐又敲了一下,噔——嘎!那聲音大得嚇了我一跳,圈里那頭大公豬也吱嗡一聲爬起來,前腿扒著柵欄門,拿它的小眼懷疑地瞪著我。噔——嘎!噔——嘎!又是兩聲巨響,我才鬧清這是放炮仗,不是我敲的。
“誰家放炮仗哩?難道要過年了?不對不對,沒磨麥子不是過年。那就是娶花媳婦和死人這兩樣了。”
呵!這下要終于有熱鬧看了。
狗叫、門扇吱扭扭、兩個人在喊著說話、還有人在大聲擤鼻子,小村終于醒了。我躥出門去。
“三聲,報喪炮……聽響聲像在東頭,離著不遠。”
“是不是順爺爺沒了,我迷迷糊糊聽著像嬋嫂子喊了。”東鄰五道叔轉(zhuǎn)著帶吃麻糊的小肉眼望向了我。
“大妗子把俺姥姥叫走了……”
“娘——唉,這就是了……才八十八,就給叫走了,小鬼們真是瞎著急,按說這么好哩老人,活一百歲也不叫多……我瞅這閻王爺忒瞎眼八叉,不分好賴人。”權(quán)大娘對著空氣拍了下巴掌,又朝當(dāng)?shù)睾莺萃铝丝谕履?/p>
“誰說不是呀,那年我腿上的瘡,多虧貼了三爺爺?shù)母嗨幉藕谩背蟠竽镞呎f邊拿圍巾角蘸了蘸眼角。
“呵,我也是唄,這么多年,呵,咱五里三鄉(xiāng),呵,不知道有多少人,呵,都貼過他熬的膏藥。呵,不行,我得回屋拿刀燒紙。”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村莊,除了到處游蕩的風(fēng),就是小道消息跑得最快了。當(dāng)我終于拿準(zhǔn)主意去老姥爺?shù)脑鹤涌纯磿r,當(dāng)院已經(jīng)有不少人在竄忙了。從人腿縫里瞅去,那個新藍布蓋著的是不是老姥爺?他躺著怎么變短了,還直挺挺得一動不動?原來不行了就是死了,不會說話也不會動了。
姥姥穿著一身的白,頭上還箍著寬條白布,如果不是聽著她數(shù)落地號哭,我差點沒認出她來。娘也成了“白人”,在那兒抽抽噎噎地叫著爺爺。吊供的男人有行禮磕頭的,大多嗚吼三聲干打雷不下雨,女的哭得就多了,常有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被勸著架起來。照這樣看不管流不流眼淚,死了人都是要啼哭的,小孩子該不該哭呢?
其實對于老姥爺?shù)乃溃乙彩请y過的。起碼他死了,我就丟了替他打醬油醋的差事,以后可再也沒人把找回的二分錢讓我買糖吃了。于是我捂住眼,眼有些癢癢,鼻子就像撞到門插管似的有些發(fā)酸。可轉(zhuǎn)眼我又想起老姥爺逮著過一個地狗子(鼴鼠),給了大妗子家的二蛋,說下回逮了再給我,這可好,哪里還有下回呀?明明就是偏心眼子。想到這兒,我揉揉眼,打消了哭的念頭,跑到人堆里去追著炸粉條的香味走動。
“俺順大伯還是有修下,說是晌伙還吃了一海碗餃子,喝了一大碗湯,睡著覺就走了。”栓姥爺舔舔嘴咕咚咕咚咽了兩下,讓我疑心他嘴里藏著什么好吃頭。
“敢情敢情,一輩子身子骨結(jié)實,到走一點罪沒受,咱們誰能有這福呦……就是可惜了這么個能耐人,干莊稼活兒是個好把式,又會騾馬經(jīng)紀,還能行船結(jié)網(wǎng)……下河撈魚……沒個他不會的營生……”拄著棍的成舅爺一邊說一邊挪到墻根搖晃著坐下,由著墻根那層泛著白嘎巴的堿土,蹭了一身。
“要著我說,這也是老喜喪了,還是好人有好報。俺三叔這一輩子光行好了,按說有這熬狗皮膏藥的方子,要是賣錢早就發(fā)家了……還有這放花,年年做呲花(煙花的一種,學(xué)名火樹銀花),放給一個村子看,大的小的誰不說他個好哩。”
“唉,再早我還尋思俺爹也真是,不知道這輩子這是圖的么?一年到頭不閑著,冬天人家都守著熱炕頭歇了,他還背著筐頭子到處掃堿土,那手凍得跟胡蘿卜一樣裂著大口子,掃回來搗騰多少遍淋點火硝,費得那勁就別提了……還得燒炭、花錢買火藥、硫磺、鐵砂子……鼓搗半天做幾十筒花,連他幾個親小子家都舍不得給,年年一家才給上一筒,剩下的都等過十五拿到十字街放……看著這咱來了這么多認識不認識哩,我才算是明白了,俺爹這輩子還真是修了好了。”
“唉,今年年上咱村再也看不成放花嘍……”
我抬起腦袋看了看天,深藍色的天上綴著一堆星星,和呲呲花一樣鋪散著。以后那些花就要被老姥爺帶走了,我家連一筒花也得不到了呀。
想到這,我終于哭了。
作者:耿佩璽 編輯:李耀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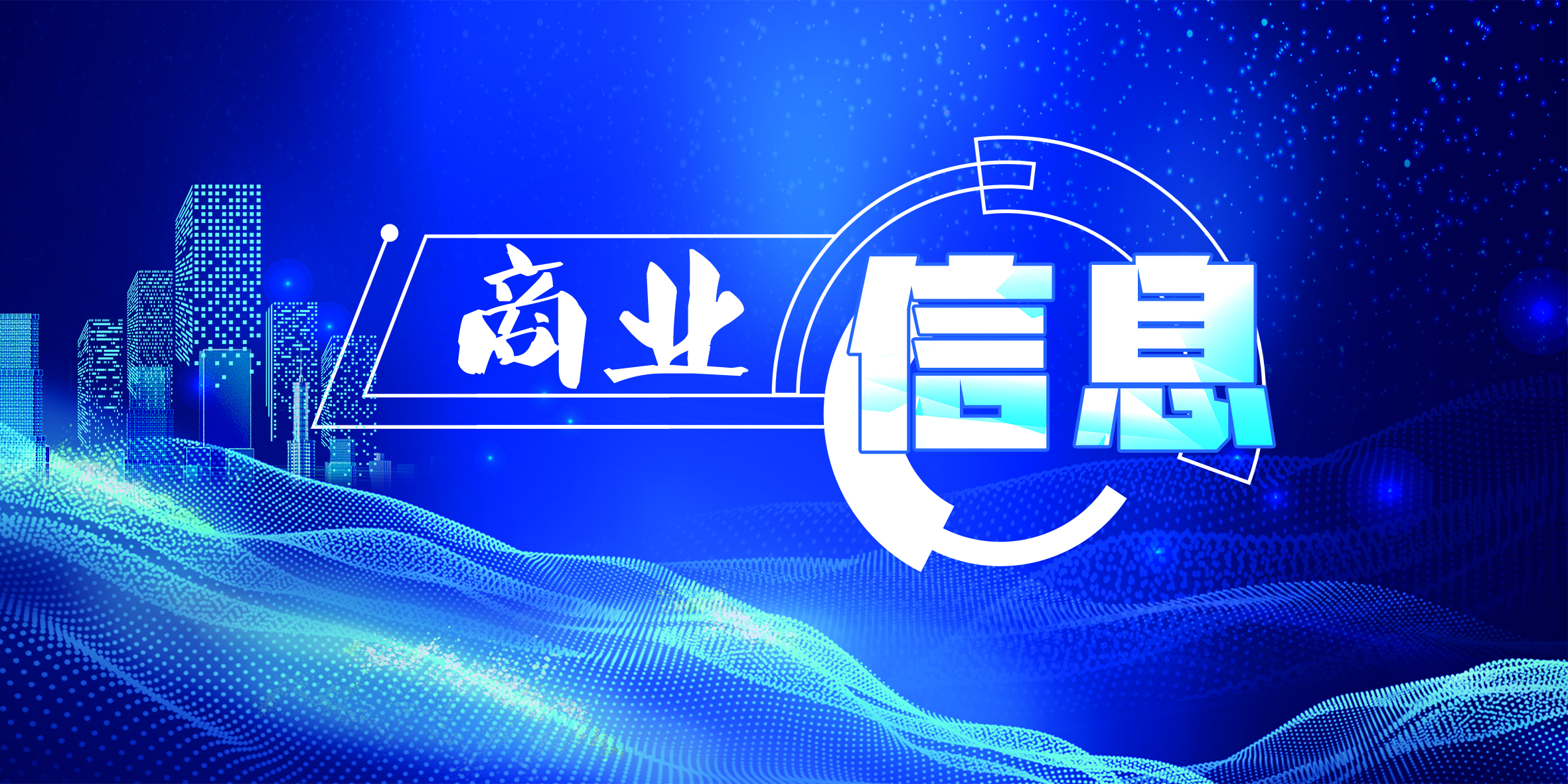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