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制作 李玲
汗與淚
“現在度日如年。并不是害怕,而是對時間的感覺出了問題,覺得這兩天跟過了一兩個月一樣。其實是心里不踏實。惦記疫情,惦記那些病人,還不如在醫院里忙著。”范立東有些困惑,不清楚自己為什么會是這樣。
從第一例隔離觀察者入院(1月24日凌晨)開始,第一梯隊16名醫護人員就失去了時間的概念,一直處于工作狀態,吃飯、休息既不規律,也不能保證時長。
“休息室就兩張床,70CM寬的那種。大家就地隔離之后,沒有辦法休息,不得已就擠在一起睡,有時一張床擠2個人甚至3個人,每次能睡3到5個小時。也不知道是什么時候吃飯,趕上飯點的時候正在忙,就顧不上,經常推遲。”范立東說。
讓所有人都覺得最難受的,是穿戴防護用具。“穿上防護服,那滋味簡直無法形容,不到1小時人就會汗流浹背。脫下來,里面的衣服都是濕的。”李志軍和不少同事近視,平時都戴眼鏡,穿上防護服就更不方便。“護目鏡外面還有防護面屏。待不了多一會兒,護目鏡上就全是水汽,我們看東西都得斜著眼睛,從鏡面縫隙去看。”
因為長時間佩戴N95口罩,大家臉頰、鼻梁皮膚被磨破,耳朵被勒得刀割一樣疼。沉重的防護用具,讓他們感到頭昏、窒息。由于長時間不喝水,沒過幾天,不少人開始上火,眼睛紅腫、聲音嘶啞。

范立東記得,自己值班那天(1月28日),來病人最多。“一晚上來了11個。有經詢問流行病學史要求過來隔離的,有因為接觸過疑似病人自己要求隔離的,我們都不能拒收。那天晚上李主任(李志軍)也在,12點左右我們就開始準備,干吧。先是說3個,放下電話10分鐘又是3個,最后又來了4個,其中一個是半植物人狀態的老爺子。”
“那天晚上確實是比較疲勞。本來是計劃第二天讓4樓的(肺三科)來協助我們,結果當天就緊急調了2名醫生過來。那一夜,沒有一個人睡過覺,一直干到天亮。”
薛軍英說,所有醫生的手機都不允許關機,必須24小時隨叫隨到。“那時主任(李志軍)已經在科里值了好幾天了,24小時在崗。這段時間事情很多,我們要隨時向他請示,他和醫院、專家組協調。”
1月25日(正月初一)晚上9點,李志軍接到市里專家組通知,去衡水市人民醫院接病人,“其實是兩例,一對夫婦。”接回來之后,薛軍英是主管大夫。“基本上是誰值班、誰接來的病人,誰就主管。如果病人太多管不過來,會分流一些。”
“開始的時候,我們可以每人負責一個病人,醫生一個班上24小時,第二天休整,護士每6小時倒班。病人一多,就做不到了。”李志軍說。

護士長郭玉丹是河北醫科大學高級護理專業的畢業生,已經在市三院工作了十多年。她從1月26日(正月初二)進了隔離區就再沒出來,接電話、發微信語音,嗓子都是嘶啞的。“我們科護理人員一直處于輪流倒班狀態,職責所在。”
執行醫囑治療、標本收集傳遞、補充領用物品、各區域衛生消毒、為病人送水送飯……郭玉丹說,護士們工作繁瑣勞累,還要克服很多心理障礙。照顧臥床行動不便的病人,要定時為他們翻身、處理排泄物。
“我們分工也不是那么嚴格,緊急的時候就一起上。幫一個病人翻身得三四個人……穿著防護服,行動特別不方便。”另一位護士長趙春燕說。
趙春燕發愁的問題,也是防護用品緊缺。“我們盡量延長在隔離區內的時間,從6小時到8小時,越來越久。”
總不喝水,上火越來越嚴重。護士韓海杰下眼瞼通紅、腫得老高,還在崗位上堅持。一天中午,護士高琦因為穿防護服時間過久、悶熱窒息,剛摘下護具就開始嘔吐。
護士劉旭盼說,因為防護用具影響視線,她們采血、輸液,需要依靠經驗去摸索操作,難度是平時的幾倍。
護士侯雅芳沒怎么說話,悄悄拭淚。她在惦記孩子。
郭玉丹忍不住感嘆,這個年過得實在太漫長了。“都在盼著疫情趕緊過去,我們能早日回家團聚。愿身邊的每個人都平安!”
偶爾停下來,第一梯隊的成員們反倒不適應了。
“這兩天就是聊天……實際上我們每天在一起這么長時間,已經快把能聊的話題都聊完了。”范立東說,市里給協調的賓館比醫院環境條件要好,大家能按時作息、吃飯,但心里并不踏實。
“疫情之前,人們說一說歇班,一天一夜不去醫院,心里會覺得不自在。我們所有人都是這樣的做派——交完班看一眼自己的病人、其他病人,同事在一起交流交流。該做的做完,能提前準備的提前準備。這樣心安。”
現在,第一梯隊休整的成員已經陸續重返崗位,再次投入到阻擊疫情的戰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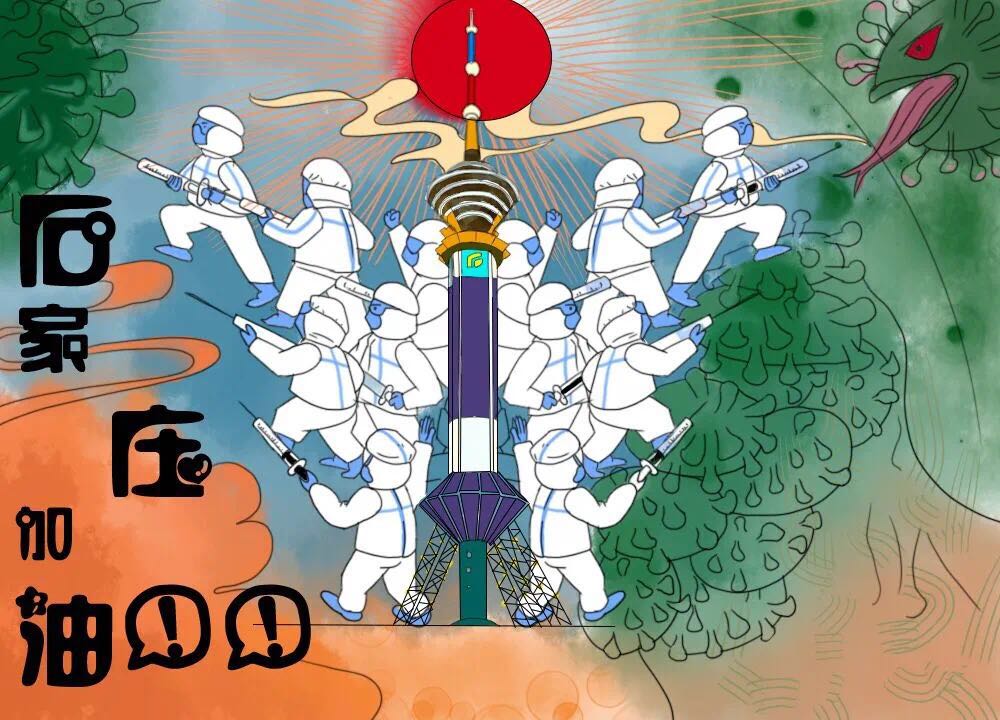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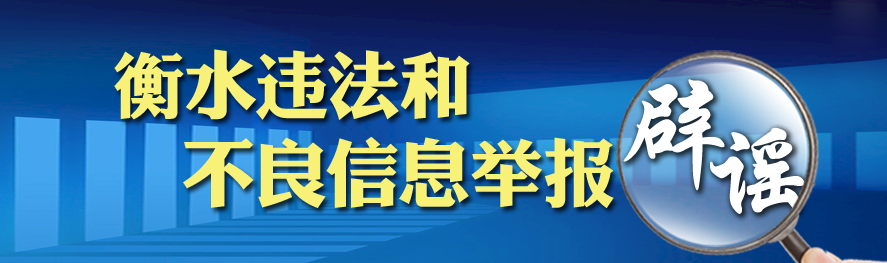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