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裂痕處照見永恒
——蔡崇達文學中的生命救贖圖譜
本報記者 趙棟
蔡崇達的文字總帶著咸澀的海風,如同閩南漁村斑駁的墻垣上剝落的灰泥,每一粒都裹挾著生命的鹽分。從《皮囊》到《我人生最開始的好朋友》,這位執筆如執刀的作家,始終在用文學的X光機掃描現代人精神骨骼的裂隙,在看似破碎的生命圖景中拼湊完整的靈魂版圖。
《皮囊》中“肉體是拿來用的”宣言,實則是蔡崇達解構生命認知的手術刀。當癱瘓的父親在咸腥海風中逐漸透明,當阿太用枯枝般的手掌叩擊自己的棺木,作者撕開了附著在肉體上的世俗價值體系。這種近乎殘酷的祛魅,在《草民》里化作老漁民被海水泡發的傷口——那些與風暴搏斗留下的疤痕,既是生命韌性的刻度,也是存在本質的隱喻。
命運在蔡崇達筆下從來不是宿命的囚籠,而是充滿張力的談判場。《命運》中神婆給出的答案,與其說是對神諭的盲從,不如說是凡人與宿命博弈的智慧。就像閩南漁民既虔誠叩拜又毅然駛向風暴,這種“信而不迷”的生存哲學,構成了作家獨特的命運觀:真正的勇者,是在看清生命局限后依然選擇縱身躍入激流。蔡崇達揭示了一個真相——生命正是在不斷的破碎與重組中走向豐盈。
蔡崇達建造的文學祠堂里,神性與煙火氣從來不是對立的兩極。
《皮囊》中母親執念修建的房屋,《命運》里繚繞香火中窺見的生死,都在消解崇高與庸常的界限。菜市場的討價還價聲可以成為存在主義的思辨現場,葬禮上的哭喪調里藏著最本真的生命頓悟。當現代文明將人物化為數據洪流中的微粒時,蔡崇達的文字始終在為每個生命個體舉行隱秘的加冕禮。
在這個意義不斷蒸發的時代,蔡崇達的創作像閩南老厝天井蓄滿的雨水,倒映著被霓虹遮蔽的星空。從《皮囊》到新作《我人生最開始的好朋友》,他始終在練習一種文學修復術——用記憶的陶土黏合現實的裂縫,讓那些被時代撞碎的靈魂,在文字的慢火煨燉中重新獲得完整的形狀。我們終于讀懂貫穿作家所有作品的密碼:生命的救贖不在彼岸,而在我們拾撿命運碎片時,掌心里殘留的溫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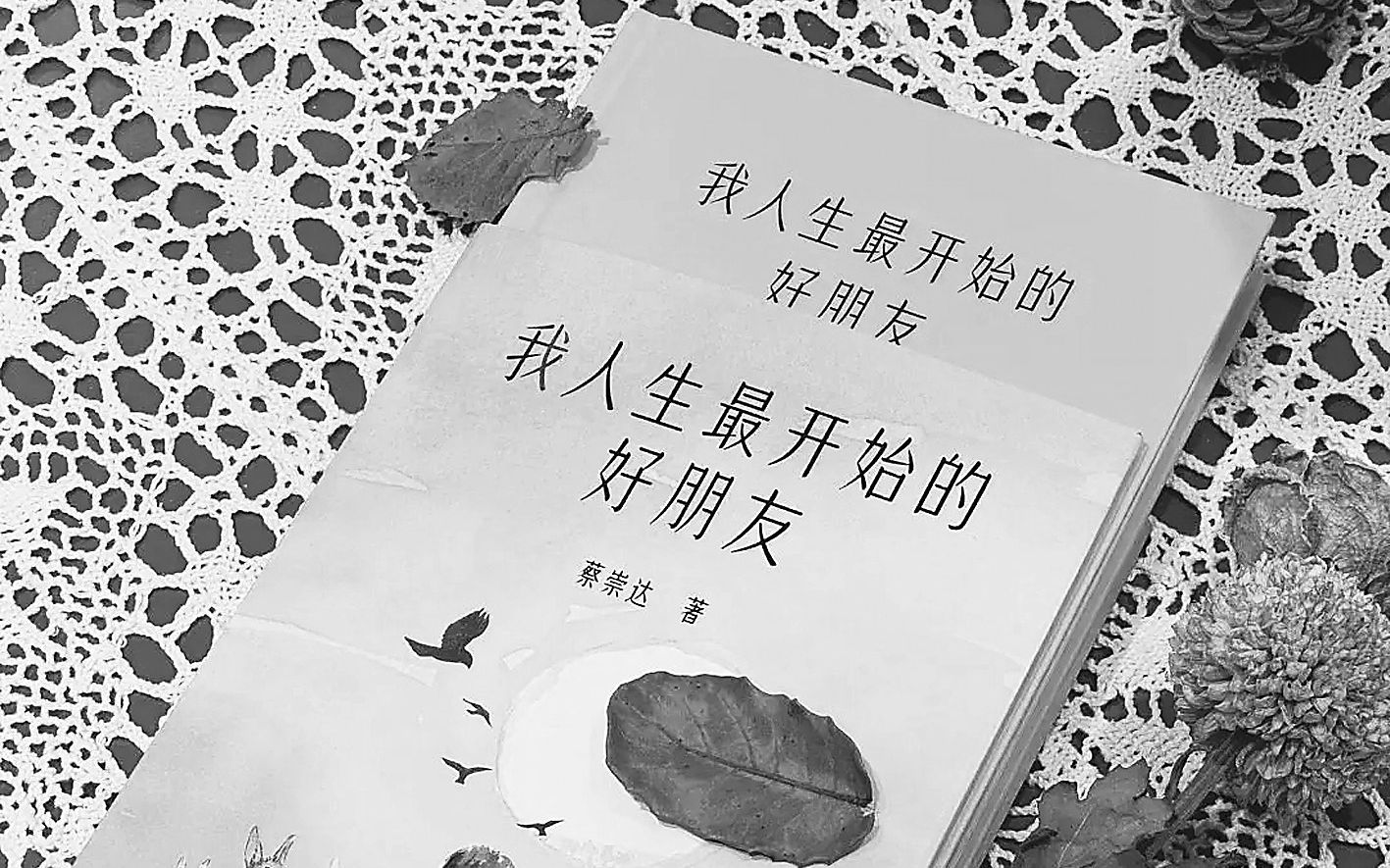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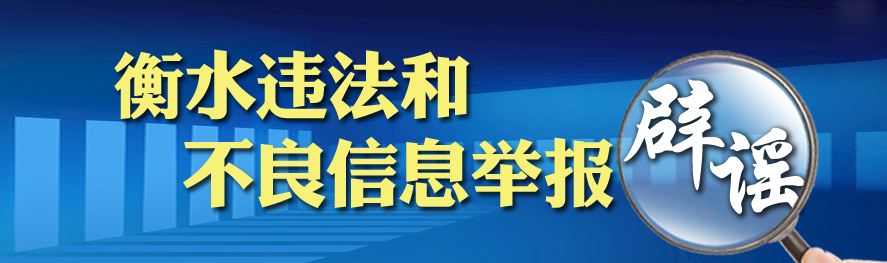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