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的夏天,每到麥收前,母親總是要去趕一次集,除了麥收用的農具和食物,母親還買回來三兩把蒲扇。
家里人口多,不能保證人手一把新蒲扇。新蒲扇淡綠色,有植物的香氣,經年的蒲扇變為枯黃,有柴煙的味道,變得易脆裂。邊沿處開裂的地方不少,為防止劃手,母親把蒲扇的邊沿用舊布包了一層邊。
土坯房子冬暖夏涼,在那沒有電扇的年代,一把蒲扇就能度過一個夏天,蒲扇的風柔和涼爽,扇累了,把扇子扔到一邊,香甜地進入夢鄉。
母親很少用扇子,她覺得扇子是閑人的標志,母親也沒有時間閑下來扇風。她每天起早下地,八九點鐘才回來吃早飯,然后再去地里,直到晌午才回來。母親洗去汗水和灰塵,然后和面烙餅或是搟面條,忙活一家人的飯菜,等到我們陸續進家,總能吃上現成飯。
那時候常有鄰居們來串門,遇有坐下來聊天的,母親總是伸手遞過扇子,父親則第一時間沏上茶葉水。在他們看來,扇子和茶水就是最高的禮遇了。
我們的中午飯常常在大門過道里吃,過堂風很涼快,影壁墻前的大槐樹樹蔭濃密。我家住村口,每天從門口路過的人絡繹不絕,父親母親熱情地和大家打招呼,一頓飯吃下來,不知道能遇到多少人。有的孩子在門外徘徊,家里大人下地還沒有回來,母親就讓他們坐下來,遞過一角餅或一個饃饃,讓他們邊吃邊等。有一次母親正切西瓜,碰到隔了幾個胡同的三爺爺路過,忙讓三爺爺吃西瓜。三爺爺邊說著“不不不”邊回家走,母親匆忙切下一塊兒西瓜,竟忘了放下手中的菜刀,一手托著西瓜一手提著菜刀攆三爺爺,一直追到三爺爺家的胡同口才追上。母親跑得上氣不接下氣,三爺爺非常不好意思地接過了西瓜。回來后,母親說三爺爺是實在人,前幾天還幫咱們家修了電燈的開關。母親的臉上淌著汗珠,拿起扇子扇了幾下,像是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似的,露出欣慰的笑容。
晚上,清掃過的院子里灑上了水,暑熱退去,飯后拿一把扇子躺在地上的布包袱上,愜意無比,不但涼爽,還能驅蚊子。母親常常扇不了幾下扇子,就睡著了,她從早忙到晚,實在是太累了呀。
母親沒有多少文化,她有著樸素的勞動觀念和善良大方的實在心腸,從不嬌氣,以“鐵姑娘”為偶像,以干活多、力氣大為自豪。
后來家人外出做小生意,母親舍不得用煤氣,一直用煤爐做飯。炎熱的夏天,廚房的爐子也沒有停過。每次我回去,母親總是在爐子旁做“差樣兒”的。放上小鐵鍋打水煎包,火焰總是上不來,母親就往爐膛里放進一兩個棒核,父親坐在旁邊的馬扎上拿一把破扇子扇風,鍋里的火候一會兒需要大火一會兒需要小火,母親不斷地指揮,父親不錯眼珠地盯著火苗。一鍋金黃的水煎包終于出鍋了,那充足的韭菜豬肉餡透過面皮,浸著油汁,香氣撲鼻。父親一掃剛才扇風的煩躁,擦擦臉上的汗水和嗆出的眼淚,喜笑顏開地說:“你娘就是手藝好,這水煎包要是在以前,是趕集串在高粱莛上賣的。”母親趕緊補充一句:“那時哪里舍得吃純水煎包啊,得用大餅卷起來吃,俺村里有個老太太趕集回來裝了兩根高粱莛,兒媳婦大鬧不止,高粱莛上有油印,說明老太太在集上自己吃水煎包了,沒有拿回來。”
經濟條件不好時,吃一頓水煎包不容易,經濟條件好了,夏天的暑熱,也是不適宜吃水煎包的,煙熏火燎,汗流浹背。可是父母的那份興奮,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只是因為想讓他們的女兒回家后吃上一頓拿手飯。
伏天里,家里終于安了一臺空調,沒兩天,在外地的姐姐回來了,因為剛做了一個小手術,父母又從空調間里搬出去,讓姐姐在空調間里修養恢復。等到姐姐痊愈恢復,秋天到了,空調也不用開了。這年的秋后,父親突發疾病,故去了。弟弟接手了門店的生意,母親回到了老家,住在弟弟的房子里。臥室有一臺空調,母親只是偶爾開,對于電器,母親除了怕費電,更覺得累心,一把蒲扇,讓她更有親切感。扇風驅蚊,母親在重復的動作里,排遣內心的孤寂與病痛的折磨,三年后,久病的母親也故去了,剛剛60歲出頭。
從20歲時嫁過來,拉扯大我們姐弟三人,母親的生活中一直都是節儉。成年后的我每買一件新衣,必被母親數落好半天。她的概念是,有穿的,就不能買新的,沒穿壞,就不能買新的,穿裙子就不是老家人的做派。以至于那些年里,在城里工作生活的我,回老家時只穿舊衣,夏天回老家從來都是長褲。回想起來,貫穿母親40余年夏天的,是一把蒲扇,或新或舊,用或不用,一直在身邊陪伴。
“粉落空床棄,塵生故篋留。”久不住人的老家,母親的許多舊物仍在,那把蒲扇,早已布滿灰塵,紋理依然清晰,像是一道道特殊的符號,記述著母親那些年夏天的點點滴滴。
作者:劉蘭根 編輯:李耀榮







 廣告
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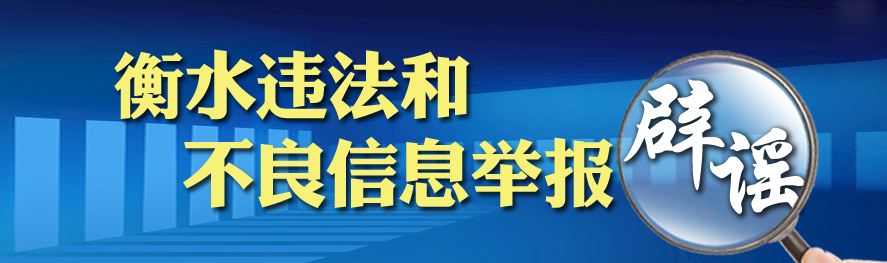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