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歲的福姑姑兩手叉腰,像一位將軍,在我們面前來回踱著步。她那雙牛眼珠子骨碌骨碌的,看樣子再一瞪就掉出來了。
“青萍,你不能去!英梅,你也不能去!”
英梅先叫起來:“憑嘛呀?”
“青萍她娘事多,到時候準埋怨俺帶壞她家閨女。英梅你動不動就可著嗓子嚎。”
“俺不讓俺娘知道,行吧?”我小聲乞求著。
英梅極具破壞性地喊叫道:“今兒不讓俺去,誰也甭去,看俺當街嚷去,哎——有人偷杏去咧——有……”
“去,去,都去!”福姑姑甩開大腳片子頭前帶路。我、英梅、愛軍、小建、榮榮5人緊隨其后,向二里地外的前光村杏林進軍。
一
春風一路向東,我們闊步向西,大片大片的麥苗綠毯一樣鋪在我們身邊。
路上福姑姑分工:愛軍和小建負責爬樹,榮榮、青萍負責拾杏,英梅嗓門大,負責望風。一旦發現有人過來,就立刻大聲唱:“小螺號,滴滴滴吹——”唱完了就跑。
福姑姑負責裝口袋,若有風吹草動,她年齡最大,跑得快,能保住勝利果實。
五月的杏樹林真是太美了,汪著露水的葉子像地里的韭菜那樣油綠,枝葉間的一串串青杏,像家中小弟的光腚球那樣肥胖可愛。一陣暖風拂過,小葉子綠蝴蝶似的跳起了芭蕾舞,蒜辮一樣壓著枝干的青杏則一顆擠著一顆當觀眾。福姑姑嘆息一聲:“來早了,杏還一個不黃呢。”
但來都來了。“你倆,上樹,揀著發白的摘啊。”福姑姑指揮著小建和愛軍。
“你倆,拾快點,注意英梅那邊,她一唱,咱就跑,尤其青萍你,到時候一定使出吃奶的勁來跑,聽見了嗎?”福姑姑的話就是圣旨,我和榮榮緊張地點頭保證著。
愛軍和小建摘得有點慢,福姑姑壓低嗓門喊:“別嘗啦,那么酸對得上口啊?摘回家還得捂一陣子呢。”那兩人才噼里啪啦往樹下扔杏。
榮榮拾得比我快,福姑姑又埋怨,“看看青萍,俺說不叫你來,非來。”
“換棵樹!你倆別在一棵樹上,摘快點!”福姑姑仰著脖子命令。
杏,開始打棗一樣落下來,八月十五棗落竿,被竿子一打,嘩啦啦落一地,就是現在降青杏雨的樣子。我抬頭看見愛軍在晃樹,他已經沒有耐心一顆顆挑著摘了。
這時,突然響起了顫抖的女高音,“紅太陽,照山河……”福姑姑一愣,大喊,“英梅唱呢?”
“不是《小螺號》嗎?”
福姑姑大叫,“別管了,快跑,來人了!”說著,一擰布袋口,扛起半布袋杏就跑。
樹上那兩人幾乎是滾落下來的,土啊傷的都沒顧上檢查,逃命要緊。我們跑得氣喘吁吁,頭都不敢回,身后一個老男人聲嘶力竭地喊:“快站住!看不打死你們,小毛賊!”
福姑姑一扔手中的布袋子,朝我們大喊:“不想死的給俺跑——”
終于聽不見追殺聲了,我們一個個癱倒在地。剛喘勻了氣,我忽然發現娘的綠頭巾跑丟了,新做的鞋也跑掉了一只——完了,等著回家挨揍吧!想回去找,又沒那膽子,我不由得大哭起來。
二
好說歹說,福姑姑答應送我回家,必要時候攔住我娘。
瞎話早編好了。
一進門,娘盯著我一身土大喝:“跑哪兒野去啦?”
“地,地里。”
“砍的草呢?”娘以為我給家里的羊砍草去了。
“俺去抱柴火做飯。”看見福姑姑丟來的眼色,我趕緊扯了個笑轉移話題。我去抱柴火,忽聽身后娘一聲驚叫:“頭巾呢?青萍,俺那綠頭巾呢?”
我嚇得一動不敢再動。娘撲上來一摑子:“問你呢,頭巾呢?俺才買的頭巾呀……”
我下意識躲了下,娘又驚叫起來:“啊,鞋呢?俺一針一線,點燈熬油的,你這個……”她罵著最難聽的話,又補給我一摑子。“去給俺找回來!找不回來打死你……”我也偷眼看福姑姑,想要求救,哪知她見勢不妙,早貼墻根溜了。
我被一下一下打急了,梗著脖子喊:“找不回來了,打死俺也找不回來了!”
“在哪丟的?俺去找。”娘停下來問。
“在,在……前光村的杏樹行……也可能在半道上。”
娘一聽就反應過來了,“好啊!合著偷杏去啦?俺叫你嘴饞!叫你丟人現眼!你怎么不跟好人學呢?跟人學偷東西,糟蹋人家杏去了,看你爸爸回來打不死你!”娘氣瘋了,扯著嗓子喊,生怕四鄰八家聽不清,我覺得丟臉至極。
這時,大門一響,我以為爸爸回來了,結果一聲熟悉的斷喝,差點沒嚇死我——“偷杏的小毛賊呢?滾出來!”
與此同時,半布袋杏被倒進我家院子,撒落滿地,一個個青杏,渾身沾滿了土,狼狽如我。
“缺爹娘管教的東西!看毀了俺多少杏!”
娘臉上火辣辣的,火氣重新被點燃,又打罵起我來。我羞憤交加,喊道:“那個袋子不是我的。”來人根本不聽我辯解,要求馬上賠錢,娘沒嘴地道歉,小聲解釋說:“她人小,一個人弄不下來這么多,肯定是別人領的頭。”娘就差說出福姑姑名字了。可人家掏出布鞋和綠頭巾問:“是你家的吧?”娘狠狠剜我一眼,小心說:“是俺家的,可杏不全是俺家偷的。”
三
正說著,爸爸回來了。杏子主人立刻添油加醋地告了狀。
爸爸聽罷,看了看滿臉淚水縱橫的我,轉身給杏主人結結實實道了個歉,然后摸著身上各個衣兜,只翻出幾張毛票,又跑進屋去湊出一疊錢來,交到那人手上,還賠上笑和無盡的好話,那人不好再罵,恨恨地看了我一眼走掉了。
我很難過,也很害怕,趕緊溜進屋去燒飯。
娘一口氣憋在心里,嚷嚷著說:“你干嘛不讓他找福子家去?肯定是那死妮子領的頭,平常就手腳不干凈,憑嘛咱自個兒賠這么多錢?”
“唉,福子也怪可憐的,年底就得給她哥換親了……咱放過那孩子吧。”
娘一肚子氣地轉向我,說:“對,人家的孩子咱也管不著,咱自個兒的孩子可不能慣著。”
我恨不得隨著灶膛里的熊熊烈火而去。
爸爸聞言虎了臉,眼光刀子般射向我,我仿佛看到火苗子躥了過來,他兩大步走到我跟前,我閉了眼睛,等待著大巴掌落下。
半天沒動靜。忽然,一只大手輕輕落在我的頭頂,那么暖。我的淚瞬間滿了眼,滿了臉。接著,他拉起我走向院子中央,一顆顆撿起地上土里滾過的青杏,低聲說:“來,拾起來,洗干凈,杏子不能糟蹋。”我的眼淚如珠子般掉落在那些灰撲撲的杏上,想起杏林里那如雨般落下的青杏,心里難受極了,就聽爸爸柔聲問:“人家的杏,就那么好吃呀?”
這才想起,我一個杏也沒吃到,壓根不知道那杏是酸是甜。現在,我只感覺到滿嘴又咸又苦的澀味,我越想越后悔,一頭撲進爸爸懷里哇哇大哭:“不好吃,不好吃,準不好吃的……爸爸,俺知道錯了。”
作者:魏東俠 編輯:李耀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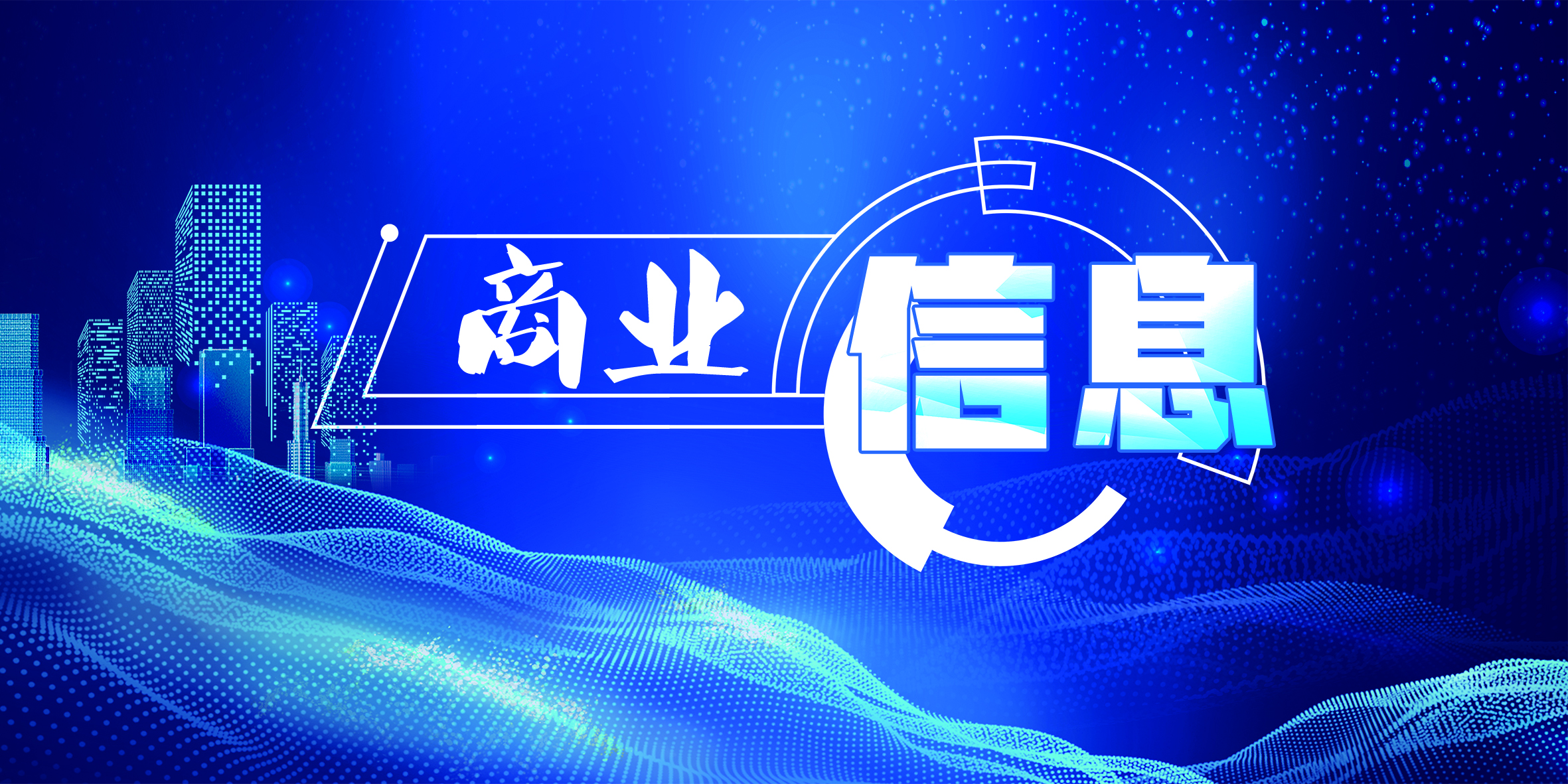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