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聲便俗
我寫過一則微博:“不可穿著白襯衣去泥塘邊。泥塘里的人是不允許有人那樣清潔干凈的。”
倪瓚很瘋很狂。這里的瘋和狂是分開說的,而不是一個詞——瘋狂。他的瘋,是自殺自殘,長釘貫耳,利斧劈頭,他想自棄那個瘋顛的世界,卻一次次都沒能死成。他的狂是他的藝術(shù),他在曲中唱:“天地間不見一個英雄,不見一個豪杰。”鄭板橋愿做他“門下走狗”,齊白石愿為他捧硯研墨。一日,他在太湖邊被起義軍首領(lǐng)張士信捕獲,因為擲筆撕絹,拒絕作畫,先吃了一頓皮鞭,又被一群人毆打在地。一介文弱書生,竟自始至終不吭一聲。事后朋友問起,他說:“不可出聲,一出聲便俗。”
知堂先生對這句“一出聲便俗”推崇得很。木心先生更是將這句奉為一生的美學綱領(lǐng)。來說是非者,定是是非人。對啊,那些泥塘里的污穢之人,恨不得惹你與他們辯白,對罵,抱摔,拖下泥淖。我們骯臟不堪,為什么偏要你干凈?
切莫上當,一出聲便俗。謹記,謹記。
無限的進步
為什么索爾仁尼琴要反對人類“貪婪的文明”和“無限的進步”,要把“悔過和自我克制”當作國家生活的準則?
葦岸說:“面對未來,人類不能再心存科學無敵的幻覺,科學雖有消除災(zāi)害的一面,但(現(xiàn)實已經(jīng)表明)一種新的科學本身又構(gòu)成了一種新災(zāi)害的起因。”
如果新冠病毒造成的全球性災(zāi)害還不足以毀滅人類,給人類以足夠警醒的話,那么在不久的將來也許人工智能會做到這一點。這不是危言聳聽。
人類開發(fā)人工智能的時間并不長,但它現(xiàn)在可以作詩、寫論文、回答問題并與人類進行簡單的溝通,甚至在計算、記憶和棋類項目上已經(jīng)超出了人類的能力。一旦經(jīng)過快速迭代,它擁有了自我開發(fā)、自我進化的能力,實現(xiàn)了自我意識的突破,那么在人類提前設(shè)定的高等物種統(tǒng)治低等物種的理念之下,它會認為自己比人類高明許多。人類若不甘心從主人變成奴隸,得到的結(jié)果只有被人工智能毀滅。
人類的進步得益于好奇心的驅(qū)使。但“貪婪的文明”與“無限的進步”將是好奇心打開的潘多拉魔盒。
蛻化
聽陳傳席先生講繪畫技藝。他先從蟬蛹蛻化成蟬講起:蟬蛹不蛻而永為蛹,至死止于爬行耳。一旦蛻殼而化為雙翼之蟬,則可聲鳴于林。緊接著他舉了白石老人為例,又分別談到齊老的兩個高徒。“若可染廢畫三千,前后畫貌不一,亦善蛻而化也;若苦禪作畫,少具才氣,然至死未蛻,故落可染一塵。”
對于繪畫,我是徹頭徹尾的門外漢,大師們孰高孰低,自然無能置喙。但從寫作的角度來看,陳先生的蛻化之說,也大可借鑒。藝術(shù)是相通的,受益受益。
回聲室效應(yīng)
回聲室效應(yīng)說的是,當你處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huán)境里,一些意見相近的聲音不斷重復,你會認為這些聲音就是事實的全部。它最大的問題不在于你聽不到不同的聲音,而是你根本不相信它們。當你遇到相反的觀點時,你的第一反應(yīng)不是好奇、傾聽、理解,而是恐懼、憤怒和敵意。
我發(fā)現(xiàn),網(wǎng)絡(luò)的便捷正在不斷強化“回聲室效應(yīng)”,并且已迅速波及到了我們的實際生活之中。這對一個人的心理成熟和道德構(gòu)建造成的破壞力,還是很可怕的。
《記承天寺夜游》
蘇軾的小品文妙在看似平常卻奇崛的收束之筆。這篇《記承天寺夜游》流傳最廣。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為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
一輪明月,兩枚閑人。百字小文,仍將繼續(xù)流傳下去。因為這樣令人向往的月夜,可能再也不會有了。在另一篇小文結(jié)尾他同樣說:“江水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
劉荒田寫:“于坡翁,月和風景都不是事,只有一個問題:閑還是不閑。閑不是‘有空’,而是能夠欣賞、體味月下境界的寧謐心境。”
我們做不來蘇軾,不妨學著做做張懷民。
嗅咖啡者
1781年,腓特烈二世頒布了一條法令:禁止國民私自進口、烘焙咖啡豆和喝咖啡。為此他專門成立一支特殊警察隊伍——嗅咖啡者。這些特警天天在柏林的大街上四處巡查,像狗一樣翕動鼻翼,搜尋獵物。
時過境遷,這樣的法令和這樣一群人,看起來多么荒唐可笑。今天的我們對某些所謂的規(guī)則條文是否產(chǎn)生過疑問——為什么要遵守?
《隨園詩話》
歷來對《隨園詩話》的評價,如同對書的作者袁枚一樣,可謂譽謗交加。
袁大才子去官后在江寧城內(nèi)營造隨園,雖然常年賦閑在野,但長袖善舞,僅靠一支妙筆,成為江南文人圈子里的核心人物。當時許多達官顯貴以請他替自家長輩撰寫墓志碑傳為榮。趙翼對他以才名攀依權(quán)要頗有嘲諷批評。《隨園詩話》也成為他媚權(quán)邀名的自留地,據(jù)傳時人多有出資買詩編入《詩話》的賄賂行為,而袁枚也都一一笑納。這自然使得《詩話》喪失了學術(shù)著作本該具有的嚴謹性。魯迅曾笑罵:“袁枚的《隨園詩話》,就不是每個幫閑都做得出來的。必須有幫閑之志,又有幫閑之才,這才是真正的幫閑。”
我倒贊成書中關(guān)于詩的“性靈”之說。資書以為詩,實在敗興之至。書中其他內(nèi)容讀讀也無妨,消遣消遣時光,至少不算糟糕的選擇。
作者:賈九峰 編輯:李耀榮


 廣告
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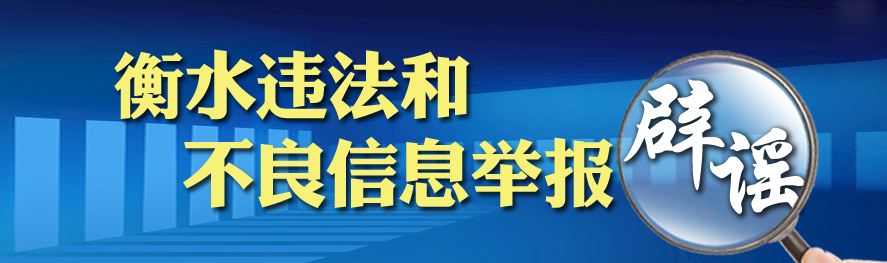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