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瀏覽“百度”,突然看到一個帖子,內容是河北大學新聞系師生征集和捐贈謝國捷教授的藏書與手稿。
據文中介紹,謝國捷教授系家學淵源深厚的安陽謝氏之后,畢業于輔仁大學哲學系,曾任河北大學中文系教授、中文系新聞專業籌備組組長和新聞教研室首任主任。頁面上還載有謝教授的手稿和一幅照片。照片上,他的面容平和慈祥,眼晴睿智有神,但腮幫稍微塌癟,嘴也緊緊撇著,似乎缺著幾顆牙齒。五十年前有緣結識謝教授時,第一印象就是他脫落了一顆門牙,不知為何也沒鑲好。
我沒上過大學,卻配合河大中文系搞過一次“開門辦學”。其唯一的帶隊人就是謝國捷教授。
謝教授帶二十多名學生來饒陽縣的五公和鄒村,搜集寫作一本和諺語有關的小書。縣委宣傳部非常重視此事,就派我到那里“全程配合”。
謝老師平易而謹慎,客氣而謙恭。他把學生分為兩組,由他和我各帶一組。至于誰去哪村,他堅持要我選擇,我自然要請他敲定,他卻連連說:“你是領導,你是領導。”說得我很不好意思。介紹他和五公村干部接洽時,見到了村黨支部書記楊同,我平日習慣以“老楊”呼之,謝教授握手時卻一口一個“楊書記”,那語氣就像面對相當級別的領導。
當時知識分子被貶為“老九”,風行的電影《決裂》竟把大學教授抹黑成只懂“馬尾巴功能”的反面典型。在那樣的社會氛圍中,謝教授的謹小慎微是可以理解的。
那是特殊時期的特殊任務,所以在確定題目時,謝教授幾乎每篇都征求我的意見,譬如批駁“人的命天注定”,題目就叫《敢教日月換新天》,批“娘們當家瞎胡鬧”的文章,題目就叫《婦女能頂半邊天》等等。雖然那些文章我都忘記了,但謝教授給學生們逐篇講解分派任務的認真態度還是如在眼前。
那些學生雖是在批判“師道尊嚴”的氣氛中入學的,但對謝教授卻非常尊重,對承擔的寫作任務也能認真對待,但因文字水平參差不齊,所以很多上交的稿子都不能令他滿意。但他對學生總是和顏悅色,循循善誘,即使指出非常明確而簡單的錯誤,也是用商量探討的口氣,從沒聲色俱厲地批評過哪一個人。有時看學生實在改不好,他就干脆另起爐灶推倒重來。他那時每天晚上都對那些半生不熟的稿子推敲刪改,把一頁頁稿紙涂得紅藍交織,面目全非。
謝教授一直沒給我分配寫文章的任務。有次我主動給他抄了兩份文稿,見他稍有閑暇,就冒昧地問:“你看現在的學生比文革前招生的怎么樣?”他愣愣地盯我幾秒鐘,很認真地說:“質量高,主要是覺悟高。”然后逐個向我介紹學員情況,說這些學生有村黨支部書記,有車間主任,有勞動模范等等。他似是坦誠地說著贊揚之語,但好像也有些言不由衷。那時的學生不經考試,都是推薦保送的。我想他作為大學教授,自然應是“近水樓臺”,就隨便問了一句:“你的孩子都上了大學吧?”不料他卻突然黑了臉,神色黯然地說有個女兒正在插隊下鄉,又在農村結了婚。談到此事,老人深嘆一口長氣說:“現在懷了孕,要生小孩了。”然后就是一陣沉默。我自知無意中觸到了他心中的隱痛。天天看著這些生龍活虎意氣風發的學生,他肯定也無時不在牽掛著那遠在農村無緣上學的孩子吧。
謝教授在交談中得知我喜歡文學,總是熱情予以鼓勵,并以浩然為例,說只要勤學苦練就會有所收獲。當時全國文藝蕭條,只有“一個作家八個戲”,宣傳浩然自然不會觸犯時忌。他說浩然只上過小學,經多年堅持才寫出《艷陽天》和《金光大道》,之前還出過十來本短篇小說。那次活動結束后,他還給我寄來一套關于浩然的研究資料和一本《杏花雨》,可惜后來丟失了。
那本小書完稿后,河北人民出版社頻頻催稿。謝教授說尚缺一篇序言,于是有學生建議請全國勞模耿長鎖作序。那時來五公的記者、作家挺多,也不時有人想借助老耿名義寫文章。但謝教授經反復考慮后說:“這樣的東西要經老耿同意才能代筆,時間緊張就不麻煩老勞模了。我看涉及兩個村的內容,最好以饒陽縣委或宣傳部的名義作序就可以。”然后對我說:“序言的起草就勞你大駕吧。”
那本由宣傳部名義作序的小書出版后,謝教授曾寄來一些,我也把一本小書存放多年,后來送給一個喜歡收藏的年輕人。
年華逝水,世事變遷,五十載光陰彈指一揮。政治云霓的浮光掠影淡去之后,久留心底的只有人性的潤澤和知識的積淀。那本小書雖然難以留傳,但參與此事卻使我對謝教授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可惜幫他謄抄文稿時未留下其珍貴的手跡,否則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捐送出去的。
作者:何同桂 編輯:李耀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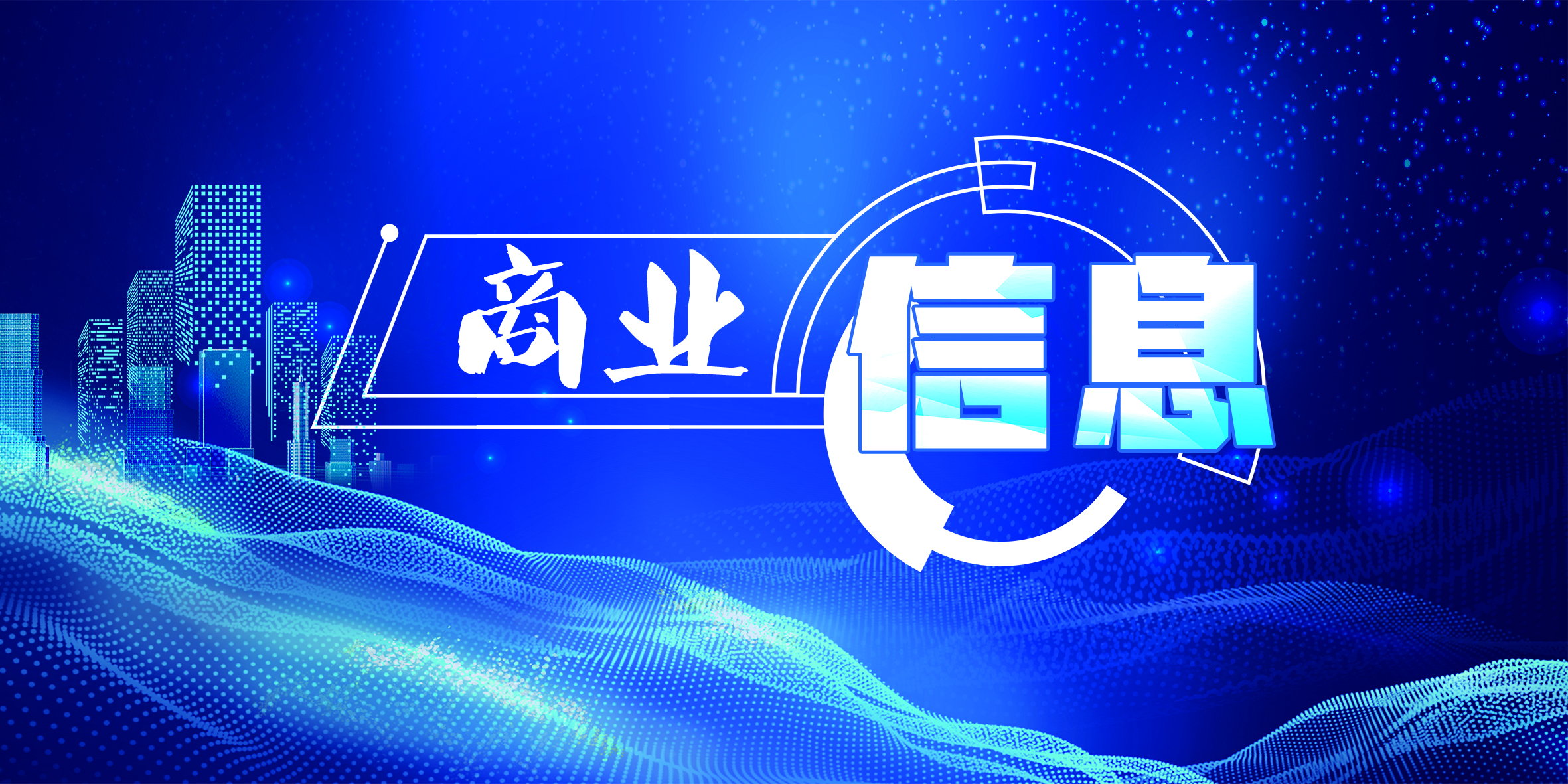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