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有閑,得空和幾個兒時的小伙伴聚了聚。在老家那條胡同里,年少的我們如脫韁的野馬,經常鬧得雞飛狗跳墻,被左鄰右舍大娘大嬸找到家里。后來我們懂事了,拿上鐮刀背起草筐,走進田間地頭以及濃密的青紗帳。我們比賽看誰先砍滿一筐青草。青草賣給生產隊,可以換取幾分錢,用來填補干癟的生活。
麥收的時候,我們經常跟著生產隊的老牛車,在一望無際的麥田里,收拾大人們割下的一捆捆麥子。那時麥子是干的,尖尖的麥芒,如同一根根鋼針,一不小心就會扎在手上、胳膊上,一陣陣鉆心地疼。趕車的老張頭手里端著三股叉,把我們用了吃奶的力氣也沒有扔到車上的麥子捆接住,放到車上,牢牢壓住。
老張頭五十多歲,圓臉,在常年風吹日曬的歲月里,生成了一張黑紅色的臉。這么多年,唯獨見了我們這些朝氣蓬勃、不知寂寞、無憂無慮的孩子們,他的臉上才會有笑的模樣。太陽很熱,就連麥田里的土也是熱的,我們身上的衣服都濕透了,細嫩的皮膚被麥芒扎得又痛又癢。可我們還是嘻嘻哈哈,你追我趕,看誰干得歡、麥子收拾得干凈。
牛車裝滿了,只有兩個人能享受高高坐在牛車上的待遇。坐在上面,整個身子都陷在麥子里,有時只露出頭。隨著牛車的晃動走出坎坎坷坷的麥田,走上了田間小路,再走上大路。那時的大路沒有現在這么寬,也沒有現在這么平坦,張老頭趕著車,手里揚著鞭子,鞭子只在空中飛舞,說什么也不會落在牛的身上,有時他和我們說著話,可我們坐在高高的麥秸垛上晃動著,看著遠方,沒有工夫和他說話,無奈他就會放開破鑼嗓子唱起來。有時唱小放牛,有時唱宋老三,只要他一唱,我們就會被吸引。就這樣,我們隨著牛車的晃動來到生產隊的場院里。此刻場院里到處是一堆堆的麥子,幾個上了年歲的老頭老太太在緊張地破捆,把一捆捆的麥子均勻地平攤在場院里。有一個老頭個子不高,干干瘦瘦的,他是軋場的一把好手。手里一桿長長的紅纓鞭時不時揚在空中,兩匹生產隊的棗紅馬在長長繩子的牽引下,很聽話地圍著他轉圈,由遠到近,由近到遠。我們站在場院邊上看著,很是羨慕,一個個心里很是癢癢,恨不得跑過去接過他手里的鞭子和韁繩,當一個很出色的場把式。我們為能站在老人身邊,雙手抓住韁繩讓馬兒圍著自己轉圈而自豪。每一次這樣的經歷,都會讓我忘乎所以,足以讓我炫耀很久。每次接過韁繩不忘討好地說:“爺爺,長大我來接你的班。”
“哈哈哈”,每到這時老頭就會撫摸著我的頭,又拍拍我的肩膀,長長地嘆口氣。我問:“爺爺你不愿意,不喜歡我?”我覺得很委屈很傷心,一股淚水涌出眼睛,也會撅起小嘴。
“好,好啊!”過了好久,老頭才輕聲說,“你們是咱村里的接班人,也是國家的接班人,不光是站在這小小的場院里打場、軋場,必須要先好好學習,走上更高更重要的崗位,去建設咱們的國家。”后來長大了才知道,老頭年輕時就參加了共產黨,在部隊負傷后,被派到地方武工隊擔任隊長,解放后由于不識字,鬧出很多笑話,就自動要求回到村子里,當了一名普通老百姓。這些年從不言說自己的輝煌歷史,只是默默無聞地干著農活,成了農村少有的莊稼把式。那時我不懂他說的話,只當他偏心眼,不讓我接他的班,我就會扔掉手里的韁繩,跑到場院邊生氣起來。
“你長大了就會明白。”老人看著我只說這一句話。
打麥場上,麥收時節要緊打、緊收、緊曬,大人們不分晝夜,甚至到家匆匆吃一口干糧,喝一瓢涼水就又趕緊忙活起來。看著大人們整天汗流浹背的樣子,我們也渴望自己到場院里干點兒活。有時我們幾個孩子喊叫著跑進場院里,不是被厚厚的麥秸滑倒就是被麥粒滑倒,這時大人們就會瞪起眼睛,大聲地呵斥我們。其實我們不是搗亂,只是出于好奇,真心實意想幫幫手。大人們不理解,我們也覺得不高興,長大了才知道在打麥場上干活很苦很累。
去年我們回老家,還特意到生產隊打麥場上去看了看,打麥場上長滿了濃密的草。此刻小村子里很靜,很多年輕力壯的都去城里打工了,街上也很冷清,很少看到孩子們。那些上了年歲的人們,也不再站在墻根,而是騎上三輪車,一天三個來回成了接送孩子們的專職司機。
這么多年了,小村在變,在發展;人們在變,在發展。記憶的閘門一旦打開,從里面走出來的人物、畫面、地址和風景,不覺間已經遠去,成為了歷史。
作者:金秋 編輯:李耀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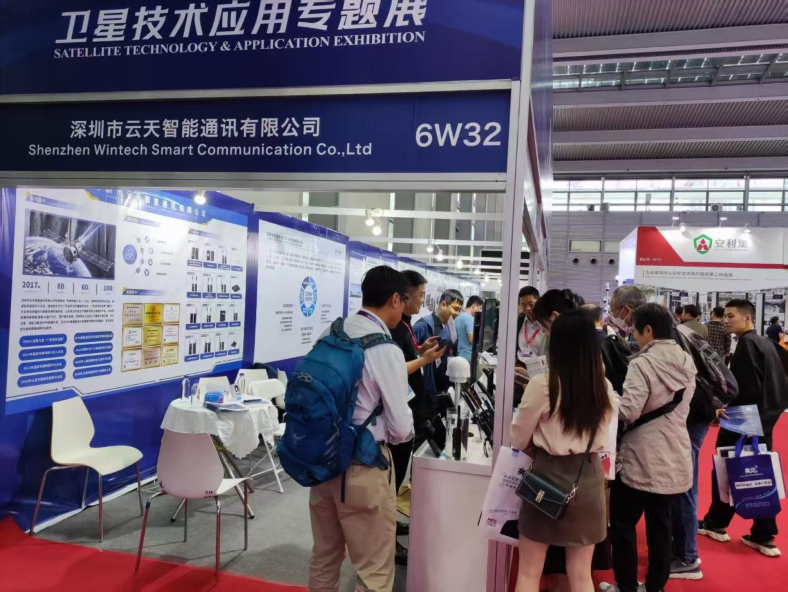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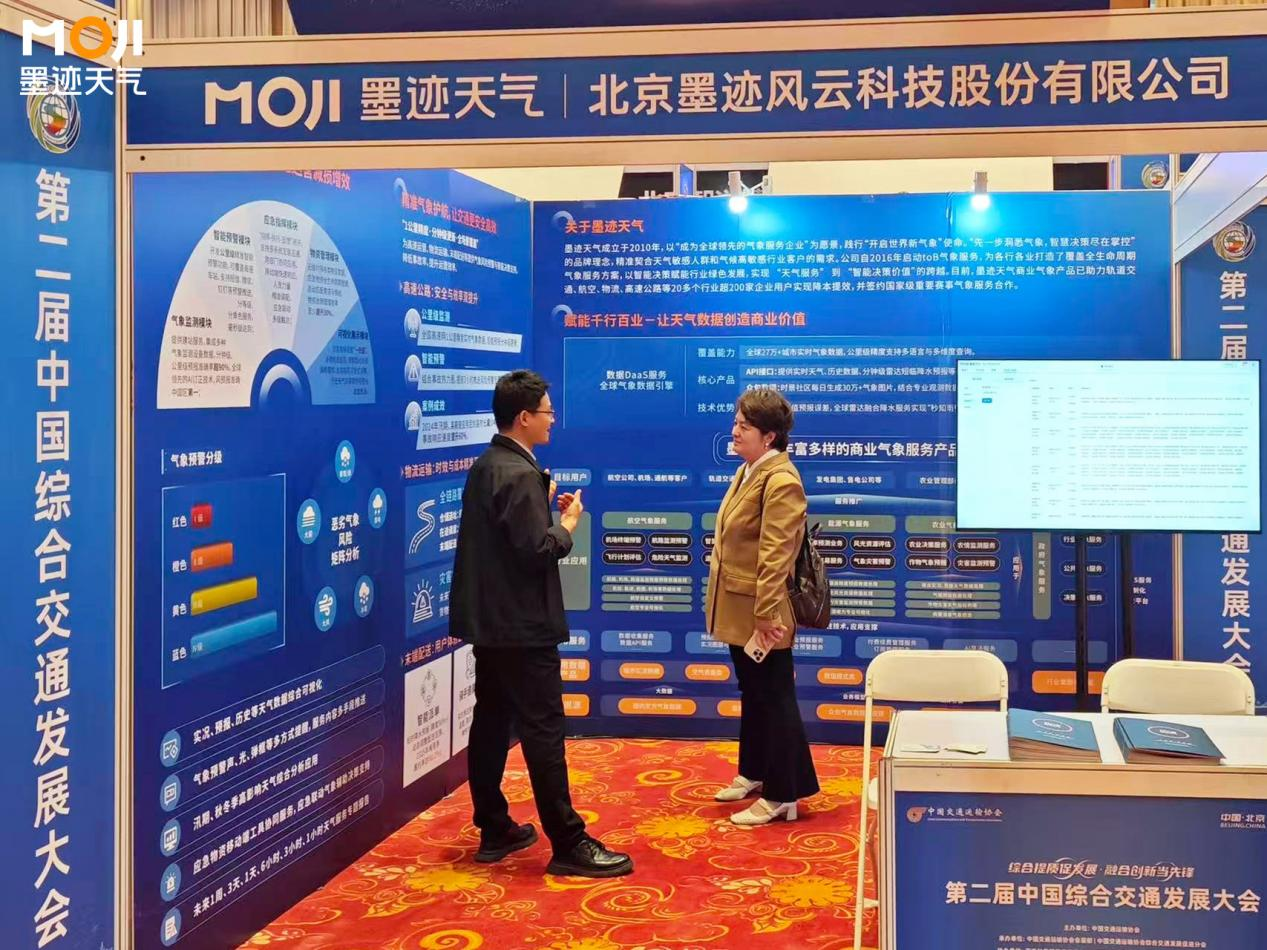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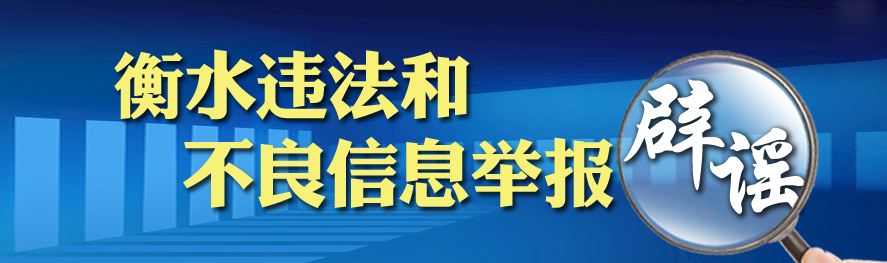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