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
天下有多少喜愛蘇軾的人,一定就有多少對章惇深惡痛絕的人。
的確,蘇軾晚年的凄愴慘景都是由章惇一手造成,擺明了,章惇就要置其死地而后快。蘇軾早年曾如此評價(jià)章惇:“能自拼命者,能殺人也!”蘇軾早就知道,章惇是個(gè)狠角色。
其實(shí)章惇的“狠”也一樣成就了他的事業(yè)。征服西夏、攻滅吐蕃、開拓西南,他做成的每一項(xiàng)功業(yè)都讓我們在孱弱的北宋時(shí)代看到了復(fù)興之光。身為密友的蘇軾在信中不乏由衷地贊嘆:“軾始見公長安,則語相識,云:‘子厚奇?zhèn)ソ^世,自是一代異人。’至于功名將相,乃其余事。”平公而論,政績考核,章惇的確勝出蘇軾一籌。
關(guān)鍵問題出在北宋新舊黨爭的反復(fù)無常。正因?yàn)闊o常,才能讓我們看到在波詭云譎的政壇上人性的反復(fù)。以蘇軾和章惇的胸懷見識,本來他們都有超越這道鴻溝的可能。我們知道,在蘇軾眾多的奏議中并非一概否定新法秉持舊法,從而使得舊黨對他亦是不冷不熱。而章惇更有“烏臺詩案”中,在舊黨選擇沉默面前挺身而出怒斥王珪勇救難友的大義之舉。那么,過命之交如何演變成了奪命兄弟?其實(shí)轉(zhuǎn)變的節(jié)點(diǎn)卻是蘇轍的《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
神宗去世后,高太皇太后垂簾聽政,反對新法的司馬光重回中樞。章惇首當(dāng)其沖,成為舊黨圍攻、彈劾的主要目標(biāo)。對于其他人惡毒刻薄的攻奸,章惇或許早有意料。但蘇氏兄弟也加入到“惡攻”行列,應(yīng)該是他始料未及的。蘇轍在奏章中罔顧事實(shí),將司馬光變更免役法產(chǎn)生的弊端,一并歸咎在章惇身上,夸大其辭,力加撻伐,必欲將其逐出朝堂。
如果說弟弟寫文章哥哥或不知情,還是章惇貶謫路上僅剩的一絲溫暖,那么蘇軾其后所上《繳進(jìn)沈起詞頭狀》,無疑為這段危在旦夕的友情補(bǔ)上了絕情的最后一刀。后面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哲宗親政之后,章惇復(fù)位,蘇家兄弟的噩運(yùn)已是萬劫不復(fù)。
“端王輕佻,不可以君臨天下。”章惇一句話沒能挽回大宋江河日下,卻再一次將自己送上黜途。與此同時(shí),蘇軾卻渡過瓊州海峽走在招回的路上。在二人命運(yùn)又一次反轉(zhuǎn)之時(shí),他特意為章惇兒子寫去一封書信,其中道盡安慰勸勉的話語。世人皆稱這是蘇軾的寬容大度,我獨(dú)以悔悟自新觀之。
我愛蘇東坡。因?yàn)檫@愛,我選擇理解并原諒章惇。
本雅明
漢娜·阿倫特對本雅明有過一段評價(jià):“本雅明學(xué)識淵博,但不是學(xué)者;研究過文本及其注釋,但不是語言學(xué)家;翻譯過普魯斯特和波德萊爾,但不是翻譯家;對神學(xué)有深厚的興趣,但不是神學(xué)家;寫過大量的文學(xué)評論文字,卻不是批評家……”
由此我聯(lián)想到寫作,聯(lián)想到諸多堪稱經(jīng)典的大師與作品。你學(xué)朱自清,學(xué)到最好你也只能是朱自清。你學(xué)魯迅,學(xué)到最好你頂多只是魯迅。你永遠(yuǎn)不是你。寫作之人當(dāng)牢記——本雅明什么都不是,但他卻是本雅明。
作品
今日讀到德國作家托馬斯·曼的一句話,心中頓感釋然。他的原話是:“終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
去年九月底,我終于第二次寫完了長篇小說《金色寺院》。但我一直在糾結(jié),自己為什么不能寫得更好一些。這樣的苦惱也許來源于我對自己能力認(rèn)識的不準(zhǔn)確(只有先完成,才具備了修繕的可能)。不過讀了這句話,我可以釋然了——完成就是好的。
關(guān)于一部小說的命運(yùn),我曾經(jīng)寫過一條微博:作為一名寫作者,作品完成之后,你的使命也已經(jīng)完成了。至于作品能不能出版面世,能不能流傳,能不能轉(zhuǎn)化成影視作品,能不能達(dá)到你創(chuàng)作時(shí)的初衷,那都是它的命運(yùn)。我們絕不能為了出版,為了流傳,為了拍影視作品而避諱,而隱晦,而放棄初衷!
糧食
寫作是一種寂寞而又誠實(shí)的生活。這與農(nóng)民種地很像——?jiǎng)趧?dòng)的辛勤、收入的微薄和身份的卑微。那么寫作意義何在?我們?yōu)槭裁催€要寫下去?
糧食的樣子何其相似!吃飯的人根本不可能分清哪一粒糧食是哪一位農(nóng)民種出的果實(shí)(自然這事從來沒人關(guān)心),但人類會(huì)因?yàn)榧Z食的營養(yǎng)活命下去,從而繁衍并生生不息。要我回答,這也許可以看作寫作的意義,潛意識中是我埋頭寫作的動(dòng)力。
我文學(xué)
第一次見識到對于文學(xué)的分類是這個(gè)樣子:我文學(xué)和你文學(xué)。所謂“我文學(xué)”,是指不管周圍的人,只表達(dá)自己想要表達(dá)的東西,至于誰聽誰不聽以及誰聽得懂,作者并不關(guān)心;“你文學(xué)”指作者會(huì)有意識地做一些商業(yè)上的迎合,更關(guān)注寫作對面的“你”喜歡什么。
以我為中心,還是以你為中心,似乎也可以看作嚴(yán)肅文學(xué)和通俗文學(xué)的分水嶺。當(dāng)然這二者并行不悖,在任何時(shí)代的寫作中都有互通互融。但分界線始終還是存在的,有的作品一眼便知。
徐霞客悖論
我們現(xiàn)在把徐霞客捧得這么高,無非是看中他的游記中體現(xiàn)的科學(xué)精神。如果他的游記失傳了,我們還會(huì)如此追捧這個(gè)一事無成的“無業(yè)游民”嗎?
下面這段話一定要抄錄下來,作為我們抵御世俗世界的小小盾牌。
“總有一些超越世俗的無意義的事情,總有一種純粹的內(nèi)心需求,孤懸著,無人理解。哪怕極少數(shù)人走出暗室,看到了陽光,大多數(shù)人也不會(huì)認(rèn)為陽光下比暗室里溫暖。人生的標(biāo)準(zhǔn)化是從標(biāo)準(zhǔn)答案開始的。你應(yīng)該活成什么樣子,什么時(shí)候應(yīng)該干什么事,這些都有標(biāo)準(zhǔn)答案。每個(gè)人都要對照標(biāo)準(zhǔn)答案作答。”
徐霞客篤定屬于極少數(shù)人。他已經(jīng)逾越了標(biāo)準(zhǔn)答案的范疇,用一生來自行答題。可是《徐霞客游記》能流傳下來,實(shí)屬極大的偶然。不是每個(gè)走出暗室的人能夠如此幸運(yùn)。
作者:賈九峰 編輯:李耀榮


 廣告
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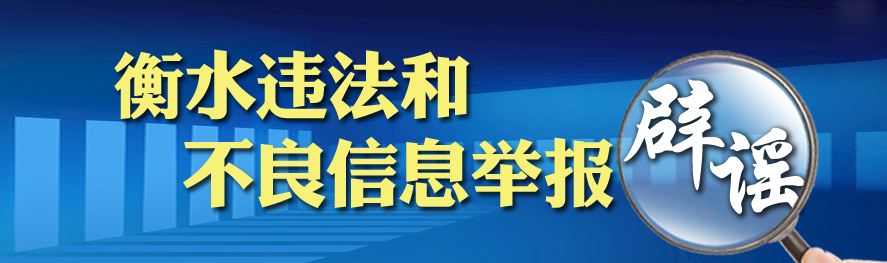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