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華是我國(guó)首部《孫犁年譜》的作者,也是孫犁晚年密切交往歲數(shù)最小的忘年交。《孫犁年譜》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后連續(xù)兩年好評(píng)如潮,被各大報(bào)刊稱為“研究孫犁的拓荒之作”“是對(duì)孫犁最好的告慰”。中科院文學(xué)所《人文》學(xué)習(xí)集刊主編祝曉風(fēng)說:“孫犁逝世二十年后,才有這樣一部年譜問世,這本身就非常有意義。”“可以簡(jiǎn)單這么說,孫犁在文學(xué)史上有多大意義,《孫犁年譜》就有多大意義。”
此書剛剛出版,我就非常榮幸獲段華先生寄贈(zèng)一部,反復(fù)研讀后頗多受益,所以一直想向他當(dāng)面請(qǐng)教。今年居京小住,就鼓足勇氣提出這個(gè)要求,他熱情地在百忙中撥冗安排,滿足了我這個(gè)老“犁迷”的心愿。
段先生主持著一份全國(guó)性報(bào)紙的編務(wù),又恰逢京城抗洪的關(guān)鍵時(shí)期,這些日子工作繁忙會(huì)議很多,所以他把會(huì)見安排在一個(gè)下午。那天我在他辦公室待了不過兩個(gè)小時(shí),卻多次有人敲門送審報(bào)樣,或請(qǐng)示簽字。看他如此忙碌,我兩次欲起身告辭,他卻頻添茶水,執(zhí)意執(zhí)留。我自然更加珍惜這次難得的機(jī)會(huì),渴望多分享他的過往經(jīng)歷和治學(xué)為文之道。
一部《孫犁年譜》,傾注三十載心血。段華在中學(xué)時(shí)期,從學(xué)校閱報(bào)欄看到孫犁的散文《青春余夢(mèng)》,就一字一句全文抄錄,并寫成題為《樹與人》的閱讀心得,發(fā)在剛創(chuàng)刊的《中學(xué)生閱讀》上。恰好該刊主編何寶民到段華所在的學(xué)校演講,就鼓勵(lì)他與孫犁通信或赴津拜訪。16歲的段華那時(shí)已擔(dān)任淮陽中學(xué)羲陵文學(xué)社的社長(zhǎng),他用暑假時(shí)間造訪大師,得到孫犁先生對(duì)他“少年老成卻又未脫稚味”的評(píng)價(jià),親切對(duì)他談了作文和做人的道理,并題字留念,寄予厚望。據(jù)此他又寫《老人的心》刊于《河南日?qǐng)?bào)》。后來段華被保送進(jìn)入南開大學(xué)中文系,距孫犁寓所不遠(yuǎn),經(jīng)常登門受大師耳提面命,并時(shí)常為孫犁先生承擔(dān)收發(fā)信函、校對(duì)文稿、購(gòu)買書刊等服務(wù)雜事,有時(shí)甚至陪同聊天散步,成為大師晚年的知音,建立了珍貴的友誼。在這期間,他不但珍藏了孫犁簽贈(zèng)的大量新著,并寫了幾十篇評(píng)介和宣傳文章。如大師傾心寫作的《耕堂劫后十種》,段華都有孫犁先生的簽字本。他說:“只有一本《曲終集》沒有簽名。因那最后一本書老人沒給任何人簽過。”段華還多年在書攤和網(wǎng)站下大力廣泛搜求孫犁軼文,認(rèn)真考據(jù)鉤沉,弄清每部著作的版本情況,每篇文章的發(fā)表時(shí)間和原發(fā)報(bào)刊。多年來他收藏各種有關(guān)史料書籍包括晉察冀和冀中區(qū)的各種資料上千冊(cè)。在此基礎(chǔ)上反復(fù)研究考證,梳理出孫犁第一次發(fā)表文學(xué)作品,第一次發(fā)表文藝評(píng)論,第一次署名孫犁,第一次收藏線裝書,第一次入選中學(xué)課本,第一次撰寫“書衣文錄”,第一次作品譯為外文;考證出孫犁是最早寫抗日地道站,最早寫白洋淀軍民聯(lián)合抗戰(zhàn),最早寫區(qū)村和連隊(duì)文學(xué)課本,最早寫解放區(qū)土改運(yùn)動(dòng),最早寫重視工人作家培養(yǎng)等等。他還發(fā)現(xiàn)未收入全集的佚文佚信五十多篇(封)。
談到孫犁的著作和文章,段華都是成竹在胸如數(shù)家珍。例如孫犁的散文《戰(zhàn)士》和《蘆葦》,原來人們都不清楚原發(fā)何處,段華在搜求舊書刊時(shí),在網(wǎng)上花五千元買到四本《北方文化》,見到這兩篇署名“紀(jì)普”(孫犁筆名之一)的文章,才得以確認(rèn)首發(fā)報(bào)刊。談話中我提到上高小時(shí)讀過一本《河北文學(xué)》,其中有篇大師的《業(yè)余創(chuàng)作三題》。段華立即說:“這本書我有,收藏在家中。”
說到這里,我站起來瀏覽靠墻的一列書櫥,見里面擠滿了各類書籍和資料。尤其顯眼的是十來本《孫犁全集》,每本冊(cè)頁(yè)間都夾著許多卡片和紙條,顯得鼓鼓囊囊而又有條不紊,那是他閱讀時(shí)寫下的心得備忘和要點(diǎn)標(biāo)記。我想這應(yīng)是“年譜”寫作的一項(xiàng)基礎(chǔ)工作吧。他說迄今為止,他對(duì)所能找到的孫犁先生著作全部通讀十遍以上,許多重點(diǎn)篇章甚至讀了二三十遍。
見我在書櫥前駐足,段華說:“這是一部分資料,珍貴的書籍多數(shù)都在家存放著。孫犁先生的贈(zèng)書都在家里,還有你們那本《孫犁在饒陽》我認(rèn)為很有價(jià)值,和孫犁先生的贈(zèng)書放在一起了。”那天回家以后,他還把存放那本書的書架拍了一張照片發(fā)來。尤其令我感動(dòng)的是,我們寄書時(shí)寫的一封信他也仔細(xì)存放。他說孫犁在饒陽土改是一生的重要時(shí)期,對(duì)其思想和創(chuàng)作產(chǎn)生著重要影響。所以自己在2000年曾去東張崗和大官亭采訪過一次,還看了孫犁先生的舊宅院——那些年,他以田野調(diào)查的方式,造訪孫犁先生寫過的地方,走訪孫犁先生寫過的人物,聽與孫犁先生有交往的人談大師等,留下了大量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可惜我那時(shí)還埋頭公文案牘,根本沒有寫孫犁的想法,更沒著意搜集孫犁搞土改的情況。而比我年輕十幾歲的段華先生,卻提前動(dòng)手,積三十年功力,干一件功德無量之事,想來實(shí)在令人感佩!
那天談到他與孫犁的友誼和交往,我說終生后悔沒給孫犁寫過信。尤其談到《孫犁年譜》中一個(gè)叫王萍慧的作者,因《天津日?qǐng)?bào)》文藝雙月刊一篇小說得到孫犁回信的記載,我說:“1982年那期刊物共登四篇小說,我發(fā)的《玉琴》緊挨著王萍慧,可惜我沒寫信求教。”段華笑著說:“你要寫信,先生肯定也會(huì)回的。”孫犁的信件在他的創(chuàng)作中占著相當(dāng)大的比例。《孫犁年譜》對(duì)每封信的準(zhǔn)確日期、重點(diǎn)內(nèi)容和背景情況都作了詳盡記載。為說明所記的權(quán)威性,段華打開他的電腦,叫我瀏覽存檔的孫犁先生友人信件。每封信不僅信瓤頁(yè)頁(yè)清晰,連信皮也一個(gè)不缺。他介紹說,這樣的信件他收集影印存檔數(shù)百封,如孫犁老友徐光耀、韓映山等人的信件全部收檔,一封不缺。看他認(rèn)真的工作態(tài)度,叫我明白了什么叫鍥而不舍鐵杵磨針,什么是一絲不茍精益求精。
告辭之時(shí),我提出要一本書作為留念。段華先生在書櫥中找到一本2018年出的《荷花的光影》,是裝飾典雅的硬皮精裝。他簡(jiǎn)單介紹書的內(nèi)容后,略一沉思,在扉頁(yè)上認(rèn)真題道:“何同桂先生指正,此小書樸實(shí)地記錄了我與孫犁先生交往的點(diǎn)點(diǎn)滴,雖不華麗,也能見孫犁先生的音容笑貌。”
這段題贈(zèng)之語說到了我的心坎上。作為“犁迷”“荷粉”,我多年因未拜謁過孫犁大師引以為憾。去年獲贈(zèng)鈐有大師手章的“年譜”,今日又有幸得到“光影”,段華先生引領(lǐng)我尋覓著大師的足跡,又叫我看到了大師的“音容笑貌”,真是不虛此次京華之行了。
分別之時(shí),段華先生不顧我一再推辭,執(zhí)意給司機(jī)打電話要求送“一位老同志”。上車前他還深情地說:“退休以后我要沿著孫犁先生走過的道路重走一遍!”我說:“那你一定要再去饒陽一趟。我那時(shí)只要走得動(dòng),就一定陪著你!”
作者:何同桂 編輯:李耀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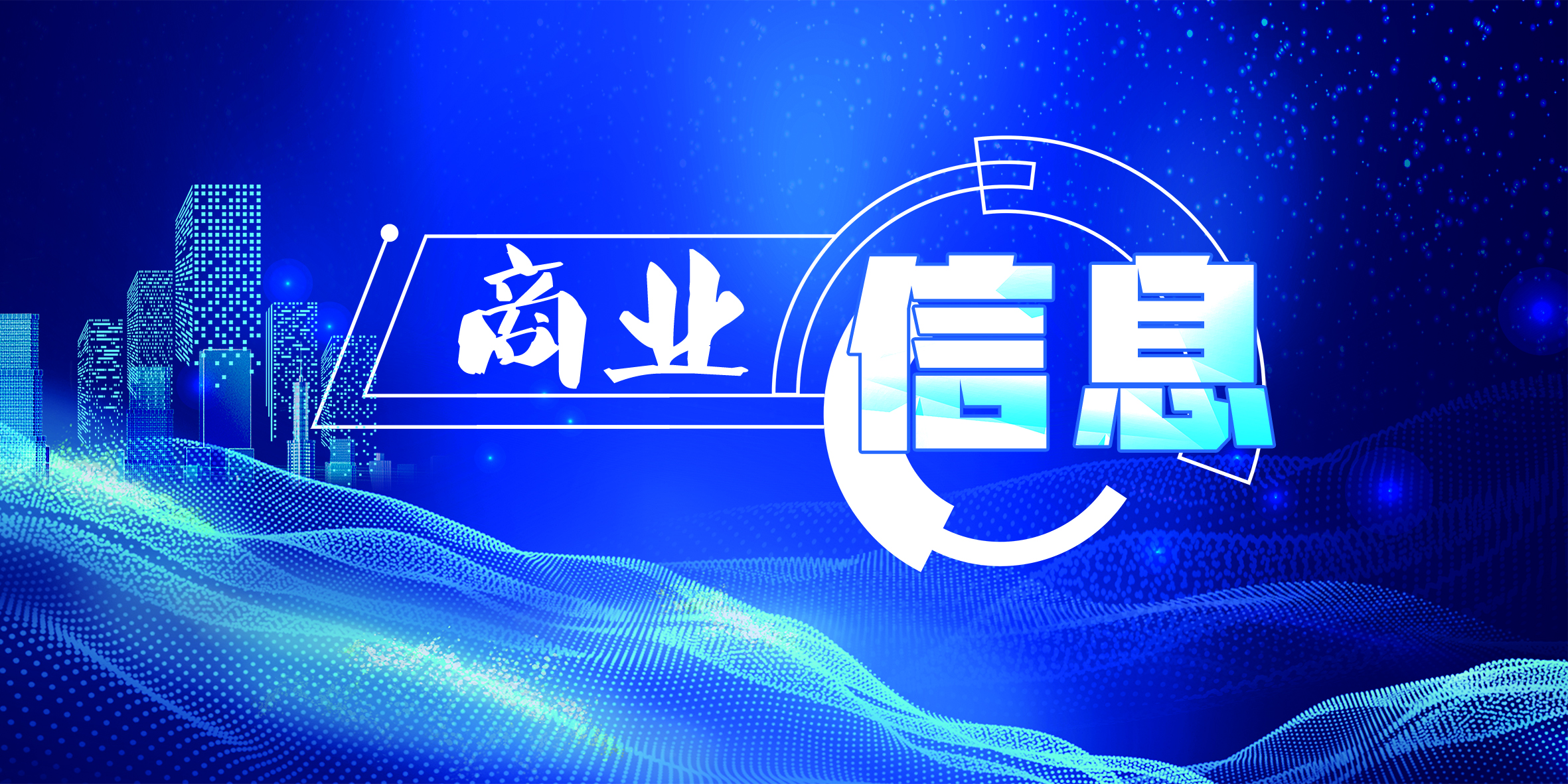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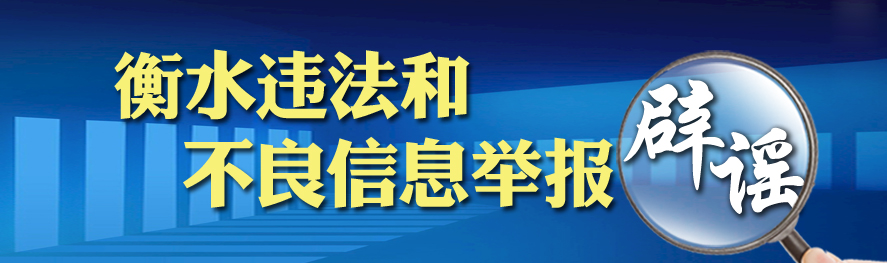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