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商業(yè)街到大學(xué)門口有十七條斑馬線,三條已經(jīng)斑駁,白線沾著零星黑塊,大小各異,微微凸起……”羅淑欣就是這樣以寥寥數(shù)語將我們帶入她寫的《斑馬線》的。現(xiàn)在,我姑且就把故事的主人公傅睛與羅淑新當(dāng)成一個(gè)人。
陳舊、平常的斑馬線,城市中屢見不鮮,但總是讓人視而不見,然而,這等微不足道的物象與能說會(huì)寫的羅淑新成為知己后,便有了她“千車裝也裝不完,萬船載也載不盡”的寫作素材和寫作可能。
斑馬線也不是平白無故地與羅淑新交好的。父親帶她去舞蹈班,外婆陪她去上學(xué),她和母親提著半米高的卷紙回家……可以說,很早以前羅淑新就與斑馬線建立了關(guān)系,也正因這由來已久的關(guān)系和印象,又巧合了她居住的樓上每每打開窗子那組斑馬線便成了她推也推不出去的風(fēng)景。于是乎,看到斑馬線,想到斑馬線,哪怕是在某個(gè)時(shí)間她忘記了斑馬線,但在意識(shí)世界里,那斑馬線,都如嘀嗒不停的鐘表,始終存在她的左右。這當(dāng)然也成了羅淑新寫作故事的源泉和動(dòng)力。
外婆蠔油炒生菜的味道她要寫,不嗆人的蒜香她要寫,飯菜的熱氣讓眼鏡蒙霧她要寫,甚至是她撩起睡衫的小細(xì)節(jié)。這些再平常不過的生活細(xì)節(jié),換一般人不會(huì)產(chǎn)生半點(diǎn)感覺的現(xiàn)象,緣何會(huì)引來羅淑新大珠小珠落玉盤似的筆下生花呢?我想這一定與她走過的、學(xué)習(xí)累了(或是說煩悶了)站到窗前能讓她看上很長(zhǎng)時(shí)間的斑馬線有關(guān)。那斑馬線是羅淑新擦燃靈感火柴的磷面,是羅淑新聚攏材料,剝離嘈雜的隔音墻,是羅淑新避免傷及眼睛的防藍(lán)光眼鏡。在這里,巴甫洛夫高級(jí)神經(jīng)活動(dòng)學(xué)說的核心內(nèi)容得到了充分體現(xiàn),即條件反射。
由此以來,她與母親、姥姥的代溝疊加;她與英語補(bǔ)課老師美思間的心理感應(yīng),以及深深淺淺、走走停停、顛三倒四的思維碰撞;她與父親的“心照不宣”;她在成長(zhǎng)過程中看到、聽到、想到,甚至是一閃而過的東西,無不接受著斑馬線的暗示或牽引,甚至是恰如其分地煽動(dòng)。因此,我不能說斑馬線給了羅淑新什么,但我能說斑馬線是羅淑新的一小時(shí)生活圈。
以利益獲得為標(biāo)準(zhǔn),誰給了誰什么不好說清;以達(dá)到某種目的為標(biāo)準(zhǔn),誰給了誰什么同樣不好說清。就如斑馬線,它真的成就了羅淑新的寫作嗎?它真的讓羅淑新完成了絕對(duì)想要的文學(xué)表達(dá)嗎?我覺得沒有。雖然這組斑馬線在小說的行進(jìn)中時(shí)隱時(shí)現(xiàn),但它并沒有像有脊椎動(dòng)物的脊椎一樣,支撐和架構(gòu)著整篇小說的靈魂和取向——我們沒有看到能讓人物為之傷心勞力的悲痛,也沒有看到能讓人物因此興奮而念念不忘的恩惠。它只是有意無意做了羅淑新的依靠,或是說它是導(dǎo)致羅淑新自言自語的始作俑者。一如羅淑新寫過的自己那樣——當(dāng)“想說卻不知道怎么說清楚的話,小說替我說”。
話又說回來,我們?yōu)槭裁匆獣r(shí)刻守著“人物性格、背景事件、歷史站位、精神面貌與時(shí)代意義”的小說主題定義不變呢?為什么不可以,從輕生活的角度出發(fā)創(chuàng)造一種“輕文學(xué)”呢?如果這個(gè)設(shè)想成立,我認(rèn)為羅淑新作出了嘗試,而且很成功。她讓人想起了20世紀(jì)80年代“嘩啦啦下雨了,看到大家都在跑,叭叭叭計(jì)程車,他們的生意是特別好……”的《雨中即景》。還讓人想到了那首詼諧風(fēng)趣的歌曲《不老的爸爸》。雖然,小說與歌曲沒有可比性,但文學(xué)記錄本真生活的輕松寫法,完全能夠作為枝葉充實(shí)在文學(xué)的大榕樹上,從而讓時(shí)代的文學(xué)更加枝繁葉茂。
等寬等長(zhǎng)等距的斑馬線,從寫作的角度去談?wù)撍坪跤悬c(diǎn)垃圾,但面對(duì)寫作高手,它似乎又是很好的能源,這正應(yīng)了人們所說的,世上沒有垃圾,只有放錯(cuò)地兒的能源。小說素材的能源何嘗又不是呢?我祝愿年輕的羅淑新在寫作的道路上不斷開發(fā)新的能源。
作者:呂乃華 編輯:李耀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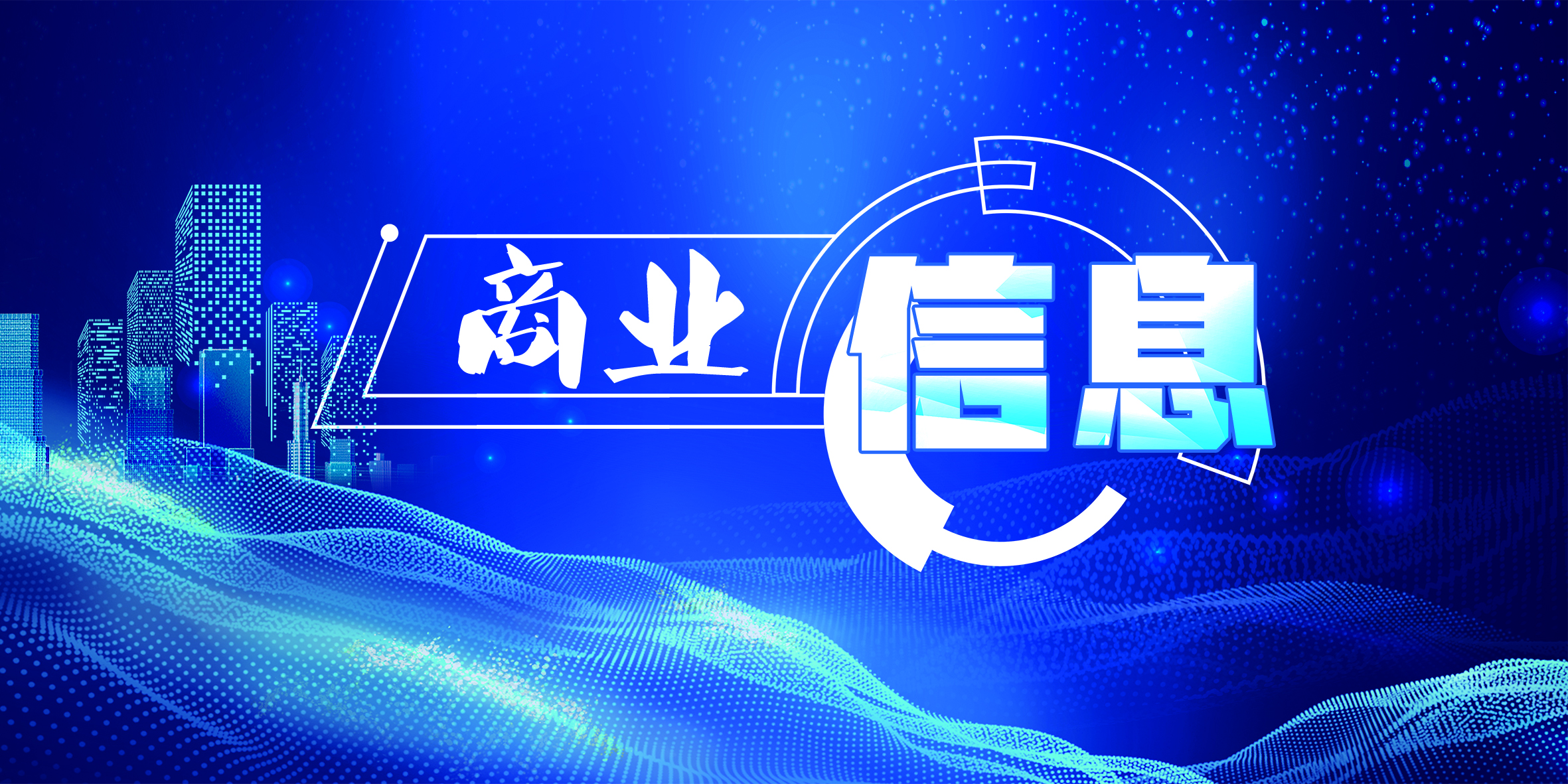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