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化時期,每個生產隊都有一個打麥場,老百姓叫做場院。場院一般都是在村邊的廢棄地上。建場的時候,要先用耙將表層的土疏松,然后潑水、撒麥秸,再用碌碡軋平。這個過程老百姓叫做“杠場”。杠過的場光滑平整,經過晾曬,十分堅硬,不易起土揚塵,最適合打軋莊稼。
每年麥收之前,都要杠場。場院里堆滿了麥捆,尖腳老太太和孩子們干不了重活兒,就在場院里曬麥子。她們把捆麥子的草繩解開,一抱一抱地將麥子撒勻,在日光下曝曬,等把麥子曬干了,男人們便用牛拉著碌碡一圈一圈地軋。曬麥子是個辛苦活兒,正午時候,陽光越毒,人們越得不住地翻場,把麥子曬得透透的、干干的。這些老太太們戴著草帽,脖子里搭條毛巾,一個個汗流浹背,臉上的汗水隨擦隨滴答,讓人不由得想起“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詩句。但是,她們都是累并快樂著的。那一滴滴汗珠就像一粒粒金色的麥粒兒,熬渴了一年的人們,眼見就能吃上白面饃饃或涼面條了,誰打心眼里不高興呢?
場院的景色是多彩的。如果說麥收場里一片金黃,顏色有點兒單調的話,那么,秋季的場院就是一張放大了的調色板,五顏六色把枯寂的場院裝點得異常漂亮。秋風送爽,各種糧食陸續閃亮登場。金燦燦的玉米(俗語叫棒子),黃澄澄的谷黍,紅彤彤的高粱,黑褐色的綠豆秧,灰黃色的大豆秸……堆滿了場院的角角落落。由于五谷的成熟期不同,因此秋天的場院不像麥收時節那樣只有五六天即匆忙收場,戰線拉得很長,從處暑可以忙到霜降。所以,這時的場院是村中人氣最旺、最熱鬧的地方。白天,人們在場里干活兒,晚上還要加班——多數是扒玉米皮、打玉米粒。吃罷晚飯,隨著集合的鐘聲落地,人們便陸陸續續走向場院。無論男女老幼,大家盤腿而坐,刺啦刺啦地扒著棒子皮,金黃的棒子伴隨著人們的歡聲笑語堆成了一座金字塔。盡管夜風有些涼,棒子皮上沾滿了露水,手指頭凍得發僵,但大家仍然是精神抖擻,用嘴里的熱氣哈哈手,不時地說著玩笑話。一陣陣笑聲驚碎了天上的星星,落下一片銀光。打棒子的時候更熱鬧,幾十口人手里都拿著一根木棍,噼里啪啦地往玉米堆上砸,棒子粒稀里嘩啦落了一地,那聲音真像打機關槍一樣脆生。
場打完了,場院又冷落下來。場院里堆了幾垛麥秸和干草。這些都是牲口的飼料。麥秸垛上大下小,為防止雨淋雪浸,頂上都抹了黃泥,形狀就像一個個糧囤。所謂干草,并非真的是曬干的草,而是對谷稈的稱呼,有的牲口棚里盛不下,也臨時放在場院里。誰家的大公雞領著一群雞在場院里覓食?它們一邊刨著麥秸垛底下的麥粒兒、小蟲,一邊不時地抬起頭來看看四周,警惕性很高。有時也會飛來一些家養的鵓鴿,它們不停地“嘚咕嘚咕”地叫著,啄食的時候看似漫不經心。麻雀的膽子最小,它們一落就是一大群,蹦蹦跳跳,啄食著落在場上的麥粒兒、谷粒兒。一有人來,便“嗡”的一聲騰空而起,有時飛到遠處的樹上,有時落到麥秸垛上,黑壓壓的一片,嘰嘰喳喳地叫個不停,似乎在詛咒誰打破了它們的美夢。人一走,又“呼呼嚕嚕”地返回來,落在地上繼續覓食。
這時的場院成了兒童的樂園。他們有的拿著竹篩子、網子、彈弓來捉鳥兒,有的玩捉迷藏、磕鐵坨、老鷹捉小雞游戲。淘氣的孩子們把干草垛或麥秸垛掏出一個窩來鉆進去,外面再掩蓋好,讓伙伴們來找,在規定的時間內找到為贏,找不到算輸。
夏天,人們買不起蚊帳,屋子里又熱,場院便成了天然的消夏“勝地”。晚飯以后,人們拿著蒲扇,袒胸敞懷,到場院里乘涼。老頭兒提著馬扎或小板凳,老太太夾著蒲團兒,年輕人則扛著用麥稈編制的篙件鋪在地上,仨一堆、倆一伙兒嘮著閑磕兒。他們山南海北,天空地闊,漫無邊際地侃著大山。老太太們自然是三句話不離本行,一坐下就說著鍋碗瓢勺鍋臺上那些陳谷子爛芝麻的話,繼而范圍越來越廣,一直說到誰家的孫子定了親,誰家的媳婦不孝順……老頭兒們叼著旱煙袋,慢悠悠地談論著農事年景以及村里的舊聞軼事和神鬼故事,聽的人時而鴉雀無聲,時而開懷大笑,時而毛發悚然,有時還熱烈地爭論著、討論著,你說是真,他說是假,甚至爭得面紅耳赤。但最終哈哈一笑,誰也不忘心里盛。而我最喜歡老人們講天文,有知識的老人一邊指點著星星的位置,一邊告訴我:北斗七星在哪里,南極六星在哪里,哪是銀河,哪是牛郎,哪是織女。漸漸地,夜深了,天涼了,大人們都回家了。剩下小孩子們在篙件上鋪開被褥,躺在上面數星星。那時的星星仿佛格外大,格外亮,數著數著就睡著了。
每年三伏掛了鋤鉤農活閑了,村里就請來說書的,這時的場院又成了文化廣場。太陽一落,性急的人來不及吃飯,就拿著凳子去場院占地方。等天一擦黑兒,場院里就擠滿了人,不光是本村“傾巢而出”,連臨近村的人也趕來聽。說書的以唱西河大鼓為多,一般男女三人,拉弦的多數是盲人,說書人常常拿他們當噱頭,博得人們的笑聲,我總覺得不太道德。但是,為了糊口,也只能這樣。道具十分簡陋,僅一燈一桌一椅一鼓一弦而已。看人到得差不多了,說書人一手打著扁鼓,一手晃動著云板,兩塊半月形的銅片伴隨著咚咚的鼓點叮叮當當地響著,再加上吱咕吱咕的弦子聲,把人帶進一個奇妙的境地。“今天晚上咱不把別的表,單說那西南上又來了一位馬能行,你若問這是哪家哪一個?他就是那個一根弦、二不楞、兔子大王惹禍精、打虎太保、包圓大將、矬子崔三胡延平!”人們隨著說書人的語氣表情,時而和風細雨,如泣如訴;時而慷慨激昂,似歌似舞;時而萬馬攢動,刀光劍影;時而花前月下,兒女情長。說的回目主要有《五女興唐傳》《楊家將》《呼家將》等,深受人們歡迎。大鼓書說得好的,抑揚頓挫,聲情并茂,一開口即博得滿堂彩。常常是這村說了那村請,說書的走到哪里一些著了迷的年輕人就跟到哪里,頭晚聽了,第二天干活兒還在津津有味地講述著那些有趣的情節。
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電影下鄉進一步活躍農村文化生活。場院理所當然成為露天影院。在場院的兩棵樹之間,拉起一張銀幕,正面的人坐不開了,很多人就站在銀幕反面去看。那時的電影比較單調,主要是新聞紀錄片、樣板戲和《地道戰》《地雷戰》《英雄兒女》《南征北戰》《車輪滾滾》等幾部國產片。后來陸續引進阿爾巴尼亞故事片《廣闊的地平線》《腳印》、朝鮮片《摘蘋果的時候》《賣花姑娘》和羅馬尼亞片《多瑙河之波》。有的影片盡管看了N次,但人們還是百看不厭,有些臺詞甚至都能背下來。電影散場了,有的嘎小子故意用朝鮮電影《鮮花盛開的村莊》著名臺詞朝著姑娘們說:“漂亮的臉蛋能出大米嗎?”
作者:宮瑞華 編輯:李耀榮


 廣告
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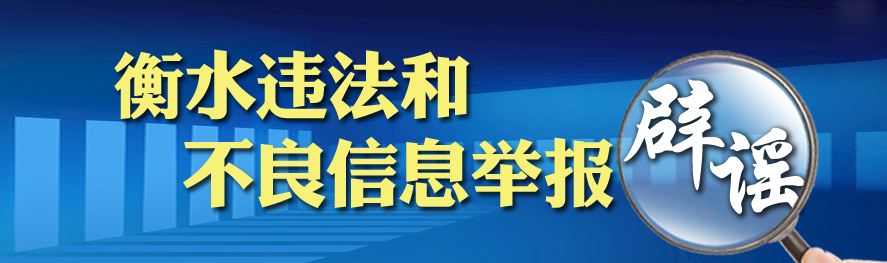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