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日的一天,信步走在鄉野上,風從耳邊輕輕吹過。記憶,也不由得讓這風吹開了一朵朵奇妙的浪花。
我的記憶,從一個小村莊開始。當時,我的父親在一個“公社”大院工作,母親是鄉村教師,在村子里教書。這是一個一百多戶,六七百口人的村子。村子有兩條東西向的街道,東面、南面是廣袤的土地。北面與外埠相連,西面是一個很大的坑塘,因此,這個村子叫“灣”。我的家在村子中間,一個窄而曲折的巷子里。三間正房,兩間東房,大門是圓的“旋”式結構,新穎而又莊重。小村莊極其普通,與別的地方沒什么二致。但是,村子的人,卻讓我不能忘記。而記憶最最深刻的,就是“黑白”大娘了。先說“黑大娘”,她是我家對門鄰居,是個寡婦,個子高高,面色黑黑,獨自拉扯一兒兩女。她家只有兩間土房,空落落的一個小院子,雖然窮困,但干凈利索,院子整潔有序,屋子窗明幾凈,室內沒有擺設,家徒四壁,一塵不染。“白大娘”呢,個子不高,白白胖胖的。那個時候,我的父親正在“靠邊站”,母親工作忙,兩個大娘成了我的“義務保姆”,整天抱著我走東串西,一刻也不離手。時間一長,村里人也不免擔心:“他家正在落難,你們離遠點吧!”但她們卻不聽這些話,說:“管他們呢,還不叫人好了。”還是像以往一樣,照顧我和我們這個家。村里的老少爺們,和我們家和得來,混得熟,也不怕我父親住“牛棚”,“靠邊站”,家里有個大事小情,還是一如既往。直到我們家搬離了這個村,還是聯系不斷,親情相牽,宛如一家。兩個大娘在的時候,我經常去村里看望她們,兩個大娘家的哥姐有事也經常聯系。有一次,母親還囑咐我把“黑白”大娘接到家來,住了很長時間。去年的時候,我到村里轉了轉,走在熟悉而又陌生的街道上,雖然這已不再是記憶中的模樣,卻還是那樣親切,溫暖。是啊,相處是美好的,唯其美好,才能使遙遠的記憶不但不泯滅,反而更加久遠。
彼時,我的父親在一個基層“公社”工作,“公社”的辦公地點是一座二層小樓,小樓坐南朝北,破破敗敗。因年久失修,人一上樓,木質的樓梯就發出咚咚咚的聲響。風一大感覺小樓就會劇烈搖晃。后來,“公社”搬到一處臨近的院子,幾排平房,小路幽遠。大院里的人,有謝阿姨、米主任、聞部長夫婦和王林大爺。謝阿姨是婦聯主任,隨和知性,她時常和我一起唱 《紅燈記》。米主任是大院的“管家”,年紀輕輕,嚴肅而又熱情,是公社大院子弟的“孩子王”,我們是他的“小跟班”。聞部長是武裝部長,威武氣派,閑暇經常帶我們去“捉鳥”,快活極了。聞部長的夫人是一名小學教師,與我母親同行,倆人說得來,重要的我是她的“學生”。因為,我雖然不到學齡,但因無人看管,父母商議,讓我去聞夫人任教的二年級做了一回“學生”。王林大爺不是本地人,說話“侉”,他白發童顏,慈祥隨和。記得他有幾回帶上我們,拿上鐮刀,背上筐子,去地里挖野菜。嗬! 那才真是天地廣闊,春意盎然! 我的玩伴,是街上一個苗姓人家的三兄弟——龍,虎,豹。其中的豹與我年齡相當,玩得愉快,我們一起在街上瘋跑,一起去坑塘“摸魚”,一起去供銷社買“小人書”。前幾日,我還與豹通話。這段短暫而又美好的時光,像是輕風送來的消息,時時閃現在我的記憶中。是呢,一切美好的事物,是心底永久的封存。
大凡學習的時光,總是離不開師尊,而我記憶最深刻的老師,姓周。周老師是我的啟蒙老師,也是我最崇拜的老師,他年紀輕輕,一表人才。我在上學的時候,寫過一篇小稿,登載在報紙上,周老師呢,就如獲至寶。從此,非常注重培養我的寫作興趣和技巧,并鼓勵我多寫多練,快出“作品”。還給我的“作品”寫了一個開篇語:日月如梭,光陰似箭,恍惚間,人生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光,這也是我要寫的理由了。但我的人生才剛剛開始,還沒有日久的積存和沉淀,我能“寫”些什么呢? 雖然那時候不知寫為何物,更不知要寫何物,但老師的期望和指導,的確讓我獲益匪淺,為我后來的工作與寫作埋下了伏筆。一晃幾十年了,我和我的老師,也從師生之恩演變成了朋友之誼,來往密切,這就是人生機緣吧! 師恩,永生銘記,這應該是每一個人人生最重要的自我標記吧!
人生的經歷,也許會有坎坷曲折,也許會有高光時刻。但愿這些經歷記憶永不折斷,永不褪色。讓它像徐徐的輕風時時吹拂,成為我們踔厲奮發的力量源泉。
作者:朱洪志 編輯:李耀榮







 廣告
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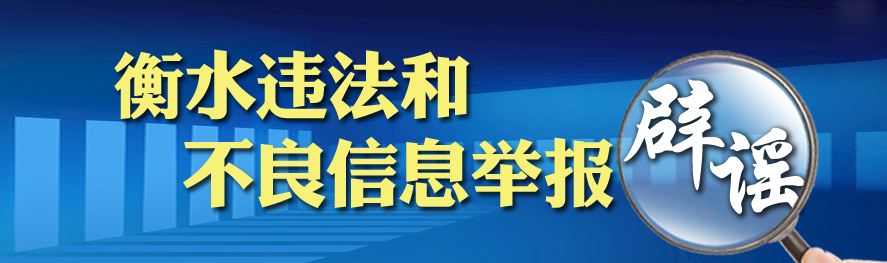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