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剛蒙蒙亮,胡同里傳來了吵嚷聲。
“你個小王八羔子,給我出來!這是你的主意吧?我現在哪里能值一個工呢?”老李頭兒嗔罵著。
村黨支部副書記聽到罵聲,來不及穿衣服,光著膀子、趿拉著鞋就朝大門跑。
“我的好叔哩,你小點聲,這讓社員們聽到了影響多不好!”副書記應承著老李頭兒。
“好叔哩!您是書記,是咱村的領頭人,這不因為您有病嗎!上級才給您安排的看護柳林,這是讓您安心養病的!”副書記明白老李頭兒的意思。
“但是,我哪值一個工,頂多記六分工,不行!六分也多了,今天晚上咱們開個會,安排一下工作。”老李頭兒斬釘截鐵地說。
在村大隊部的會議室里,11個黨員圍桌而坐,老李頭兒旋轉了一下燈草開關,煤油燈瞬間明亮起來。他點燃一支旱煙,慢慢地吸了一口,像在思考著什么。
咳、咳……一口煙沒吐岀來,老李頭兒嗆得咳嗽起來。
“叔,身體要緊,少抽兩口!”眾人勸慰著。隨著又一聲咳嗽,老李頭兒掏出手絹捂在嘴邊,手絹立刻被鮮血殷紅了。他顫顫巍巍地摸向懷里,從口袋里摸出一疊錢放到桌上。
“今天咱開個會,昨天我和縣土產公司談妥了,只要質量可以,咱的柳編產品他們照單全收,我尋思著咱還得找點活兒干,只有壯大了集體經濟,老百姓才能得實惠。張經理說他們那兒還收‘二踢腳’,這錢就用來買原料吧!你們看看有什么意見?”老李頭兒說完,擦了擦嘴角的鮮血。
眾人知道老李頭兒的脾氣,都不敢吱聲。
副書記硬著頭皮說:“叔啊!俺們大伙兒知道,這可是俺兄弟的撫恤金呀!這錢村里不能收,況且,拴子怎么辦?”他一邊說話,一邊指著依偎在爺爺兩腿中間的拴子。
老李頭兒沒有理會:“等柳編和炮仗掙了錢,一定要先解決學校課桌問題!軍烈屬也要優先照顧,逢年過節一定要慰問到,不能讓烈士流血又流淚!”
副書記也急了眼:“叔啊!你也是軍烈屬啊!您現在看病更需要錢,這錢村里真的不能收!”老李頭兒一拍桌子:“他算哪門子的烈士,又不是在戰場上犧牲的!”老李頭兒犯起了倔勁兒。“幫助群眾救火,為了保護群眾安全就是烈士!”副書記拿起錢就往老李頭兒懷里塞。
“這事就這么定了,別看現在是你主持工作,但這事兒我說了算!”老李頭兒擺起了家長作風……
多年以后,在大隊部的舊址上,拴子在新蓋的辦公室里,隔著窗戶向外望去,對面的村小學,當初靠村副業收入翻蓋了新教室,如今又從平房翻蓋成三層樓房。拴子想起了爺爺,爺爺當初那不是開會,那是在交代遺愿。現在爺爺的愿望實現了,這讓拴子又想起了送爺爺的場景:
“嬸子,這是咱村老少爺們兒湊錢買的洋灰棺材,只是委屈李叔了。”副書記拉著拴子奶奶的手安慰著。接著又說道:“您老也別挑禮,鄉親們到了飯點都回自家吃,您看看這院里的鄉親們,人人心里面都有一桿秤!”
老李頭兒出殯的時候,或許是上天也被感動了,下起了大雨。
農村有個風俗,棺材落地是不吉利的,為了避免在泥濘的土路上滑倒,抬重的青壯年全部光著腳丫……
每每想到這里,拴子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拴子哥,你帶來的錢和咱的預算都超支了,那幾根電線桿怎么弄到土坡上去?”來人向拴子問道。
“這么說,要是沒錢,咱這光伏電站還建不成了?我還真不信這個邪了,組織黨員和干部,我們抬上去!”拴子攥緊了拳頭。
“電桿可是洋灰筑的,沉著呢!這馬上又要下雨了。”來人嘟囔著。
“難道比我爺爺的洋灰棺材還沉?電站早建成一天,村集體就早一天有收入!”
“來,一二,上肩。抬重!”拴子叫著號子。
“拴子哥,虧您自己還辦公司呢!現在又當了書記!抬重是抬棺材時才說的,建光伏發電站是喜事,您這么說多不吉利!”人群中有人打趣。
“你不感覺重嗎?我們現在抬起的是信任,抬起的是擔當,你們說是不是這么個理兒?”拴子反問大家。
大伙心頭一熱,不再說話。
風雨中,這群男人打著光腳板,抬著沉甸甸的分量,一步一個腳印地向土坡走去。
作者:朱立偉 編輯:李耀榮






 廣告
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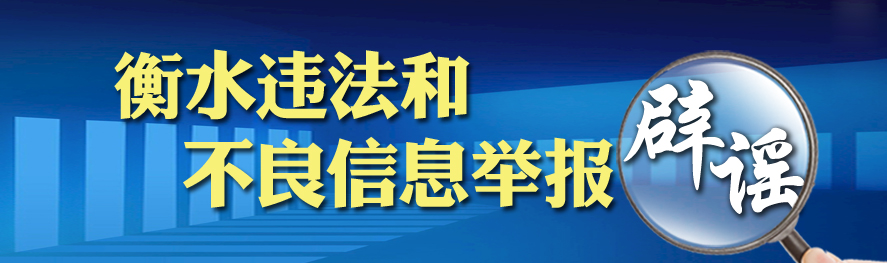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