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北京琉璃廠,不僅在中國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就連外國人都會慕名而來。它是明末清初因官員、京外趕考舉人在此逛書肆繁盛而起,被歷代文人學士視為“安身立命之所”與“京都雅游之所”。數百年來,這里曾經集散、流通和保護了大量不可估量的文化財富,成為我國傳統文化物質載體的“聚寶盆”,促進了中華文明精髓與神韻的延續。
對于琉璃廠的緣起發祥,長期以來民間就有“江西幫”“衡水幫”“老山西屋子”等之說,但也均為口耳相傳。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時年86歲的我國著名古籍版本學家、發行家郭紀森在中國書店跟筆者的一次談話中,“引經據典”并用事實和數據進行了有力地佐證后明確提出“衡水人發祥北京琉璃廠”。作為文史愛好者的我隨即將其通過報端公布于世,成為史上第一次以文字形式對外宣稱此學說。事實也證明,無論是現在地級市的衡水市還是建專時期的衡水專區,甚至是明清民國年代的直隸衡水縣,“衡水”地域上走出了一大批經營古玩字畫和古舊書的群體,他們在琉璃廠創立的字號店鋪曾占到這條街的半數以上,最高峰時竟超過九成,讓琉璃廠成為“琉璃廠文化街”。
這一學說提出20多年來,媒體、學者、政府頻頻發力已把其做出了影響力并成為一種文化現象,讓鹽堿地上沸騰起了“文華衡水”和“衡水儒商”的潮水。值此,筆者作為這一學說的挖掘人和首發者,今將其來龍去脈作如下詳釋,以回應“大儒之鄉”的“冀文化”牌。
民國初期少小離鄉進“廠”的衡水群體
1914年,郭紀森生于衡水市冀州區冀州鎮郭家莊。15歲時,因家境貧寒離開了私塾,由叔父郭恒利引薦到北京隆福寺的古舊書店稽古堂(棗強人郭喬生創立)當了學徒工,三年后出師做伙計,從此開始了八十年的販書、鑒書人生。
當時,北京的古舊書店主要集中在隆福寺、琉璃廠、東安市場一帶,廣安門、后海、西單、東西曉市、打磨廠等也有零星書攤販售。1939年,郭紀森被琉璃廠書鋪勤有堂(棗強人崔世璋創立)聘為副經理,1943年,在西琉璃廠從孟慶德手中接過開通書社,自任經理一直到解放后,主營大部頭古書和考古類圖書。1956年“公私合營”后并入中國書店,他任中國書店古書店副經理。退休后又被聘為中國書店顧問,1992年獲得國務院特殊津貼。
郭紀森畢生從事古舊書事業,從未改過行,憑借著一身過硬的“過眼學”經手流通的古籍圖書難以計數。如今全國各大圖書館和許多教授的書齋中,幾乎都有他所提供的古籍圖書資料。
我發現,琉璃廠的衡水籍人士大都與郭紀森的情況相仿,多出生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那時衡水境內的滏陽河、滹沱河泛濫,冀棗衡深等地大水成災,不少人因饑逃荒,孩子到了十五六的年齡要么成為家里的壯勞力,要么外出謀生。在當年,找關系“走后門”去北京琉璃廠卻成了一些孩子的“好”選擇。其實不然,他們年齡小,文化低,從事的又是艱深難懂的古書業,其歷程的艱難可想而知。但沒想到,這些為了糊口的泥腿子、毛孩子們很是爭氣,慢慢從這條街上的販夫走卒,通往于各地大小書肆,出入于巨賈名流書齋,逐漸熟悉了書的版本、源流、內容。他們在搜集整理修復翻印各種古舊書籍中終成大器,成為響當當的“家”,在中國古籍版本事業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書行元老首提“衡水人發祥北京琉璃廠”

1999年夏,筆者在北京采訪郭紀森(右)
1999年暑假,尚在讀中學的我,在冀州方志辦老編輯常來樹的引薦下,到北京南新華街與騾馬市大街交叉口西北角的中國書店拜訪了郭紀森,那年他86歲。談話中先生無意的一句話,讓筆者興奮不已。
“小劉也是咱衡水的!都是老鄉。”郭紀森把我介紹給辦公室里的老先生們后他繼續說著,“是咱河北人奠定了琉璃廠的輝煌,或說是河北人打造了北京的琉璃廠,并延續了琉璃廠文化,河北人當中以衡水人為主,就是咱衡水人發祥了琉璃廠!衡水人中又以咱冀州人為多。”我瞪大眼睛,竟不怎么禮貌地說:“什么?衡水人發祥了琉璃廠?您再說一遍!”老先生一愣,以為說錯了什么話。我忙解釋:“這么爆的料兒,您老繼續講講。”我這么一說,逗得幾位老先生直樂。就像小孩聽“古兒”一樣,我那么陶醉,繼續托著腮幫子,邊聽邊記。
郭紀森說,當年奉旨纂修《四庫全書》直接推動了琉璃廠書肆的形成。由于各地學者云聚京門群居宣南一帶,經常有人攜伴而行到琉璃廠的書攤搜覓圖書閱讀資料。隨著這次修書的興盛,書攤陸續升級店鋪門店,紛紛請文豪名流起名題匾,北京四九城的古舊書商和古玩字畫人等涌進琉璃廠,從此讓琉璃廠成為名副其實的文化街。
“由于河北靠近北京,來往比較便利,自明朝萬歷年間就有衡水人在琉璃廠經營的古玩字畫和古舊書店鋪。特別是到了清朝科舉廢除后就完全取代了‘江西幫’,很多親戚帶親戚、同鄉帶同鄉而來,撐起了琉璃廠的文化時代,延續了其文脈。”郭紀森說,這種傳承關系,使得不少衡水人密集來京以買賣古舊書為生,自己就是這么來的,先到隆福寺,后到琉璃廠,先當伙計,后做掌柜。
見我聽得入迷,郭老又翻箱倒柜找來一本1962年版《琉璃廠小志》。這是一部研究琉璃廠文化街沿革演變和古籍版本及市場的重要文獻,作者孫殿起是第一位有著作問世的書商。《琉璃廠小志》也是首本由古舊書從業者編撰的史志,與之前文人雅士所述琉璃廠大有不同。
孫殿起(1894年-1958年),冀州人。15歲時輟學入京學商受業于宏京堂的郭長林(字蔭甫,冀州人),后開設通學齋書店。他經歷了清末、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幾個朝代。他在經營古籍販書的五十多年中始終保持著一個習慣,凡經眼和販過的書籍,均一一記錄其書名、卷數、作者姓名、籍貫、刻印時間、刊印廠肆等資料。日積月累,他對目錄學、版本學有了較深造詣,陸續利用工作之余編成《叢書目錄拾遺》《清代禁書知見錄》《販書偶記》《琉璃廠小志》等。
百余年來,琉璃廠從業人員中衡水籍人士占相當大的比例。《琉璃廠小志》第三章“書肆變遷記”中稱:上溯道光咸豐年間,下至民國三十五年這一時期在琉璃廠開設書業店鋪的共三〇五處,而由冀縣、衡水、深縣、棗強、阜城、景縣等衡水籍人士開辦的共一百六十四處;第四章“販書傳薪記”中又稱:當時琉璃廠以經營古玩字畫為主的店鋪共一百四十六處,衡水籍開設的有六十處,以書畫裝裱業為主的店鋪共十九處,衡水籍開設的有十一處……除了《琉璃廠小志》外,明萬歷年間李誠誥的《海甸行》與清乾隆年間李文藻的《琉璃廠書肆記》也均有“衡水人在琉璃廠”的活動記錄。近年,衡水市冀州區委宣傳部編《琉璃廠的冀州人》序言引用學者研究數據寫道:“咸豐末年,冀州人在琉璃廠開設近300家店鋪,占據琉璃廠總店鋪數的90%左右。”
郭紀森也陸續給我引薦了一些人,比如古籍版本學家張宗序(深州人,16歲進琉璃廠。)、馬春懷(冀州人,16歲進琉璃廠)、古籍文獻鑒定學家吳希賢(冀州人,16歲進琉璃廠)、外文版本學家種金明(桃城人,15歲進琉璃廠)等先生。當時他們在中國書店及北京市文物局從事古籍版本的鑒定工作,也都干到生命的最后。期間,我又結識了另外一些成名成家于琉璃廠的衡水籍人士,如碑帖文物鑒定學家馬寶山(桃城人,16歲進琉璃廠)、裝裱藝術大家劉金濤(棗強人,12歲進琉璃廠)、一得閣第二代傳人張英勤(深州人,14歲進琉璃廠)等。拜訪中,我也一一懇求老先生們對郭紀森首提“衡水人發祥北京琉璃廠”一說發表意見,他們紛紛表示贊成,因為他們都是琉璃廠的活資料庫。
張英勤先生還將一份簽名加蓋手章的《一得閣傳人史記》贈我,他說:“一得閣是由安徽人謝松岱創辦,第一代傳人徐潔濱就是深州人,我作為第二代傳人于1941年進廠學徒一直干到廠長退休,長達60多年。”張英勤是領導一得閣時間最長的一位廠長,也是公私合營后的首任廠長。另外,一得閣改制前的董事長也是深州人。
郭老給筆者送來他近年手寫的《回憶古舊書業概況》《在舊書店學徒期間學習業務的經歷》《古舊書行業興衰變遷》等16頁近萬字的影印稿。無論是在當時還是現在,這些資料都彌足珍貴。郭紀森寫道:“琉璃廠書業乾隆嘉慶年間以前多系江西人經營……后以同鄉關系頗有仿此行者,遂成一集團,直至清末科舉廢除后,此種集團始無形取消,待江西幫繼起者多系河北人,彼此引薦同鄉親族子侄由鄉間入城謀生,后來如河北冀縣、南宮、棗強、衡水、深縣、束鹿等地的人逐漸多起來。”
有人說,衡水人天生愛書。其實歷代衡水人都崇文敬古,又地近京都,自然進京販書成為唾手可及的營生事之一,當然也有不少人從事“線貨”生意(土布口袋等)。到孫殿起、郭紀森這代人進駐時,衡水人已站穩腳跟,讓古舊書業成為琉璃廠的“規模產業”。
出于新聞敏感和家鄉榮譽的考慮,我根據郭紀森的口述和史料記載分析撰寫一則新聞稿《衡水人發祥北京琉璃廠》。征得幾位老先生的同意后,又聽取了地方文史專家李功和常來樹先生的建議,我將這則千余字的消息通過華北發行量最大的《燕趙都市報》發往全國。盡管稿子發出后,也有不少外地學者對其中的淵源與衍變有些微詞,但的確是衡水人撐起了琉璃廠的繁華,使之薪火傳承至今。
對于“江西幫”,是指以“金溪書商”為主的“江右書商”。他們最早在琉璃廠開設書鋪的書商姓氏無從可考,民間多以“最先在此開設書肆的是一名江西籍舉人”。孫殿起《琉璃廠書肆三記》載,有江西籍書業者身影將近20家,賣舊書的總數僅6家,多售賣新書,對版本目錄學的知識所知不多。等到后來雷夢水所著《琉璃廠書肆四記》時,其江西籍人士差不多已絕跡。
而“老山西屋子”是指山西人開的買賣。舊時,山西人在北京開店都是一水兒的山西地方人,鋪子里從不見外地人,琉璃廠的德寶齋和英古齋就是山西人所開。
衡水人發祥或打造北京琉璃廠,之前多是河北人口頭上的自詡。我查閱了新中國成立后出版的《琉璃廠小志》《琉璃廠雜記》以及《文史資料》《出版史料》《發行家傳略》《北京出版史志》《北京檔案史料》《衡水市文史資料》《冀縣文史》等文獻資料,均沒有出現“衡水人發祥或打造北京琉璃廠”字眼,只是對琉璃廠的部分衡水人開設的字號和事跡有零碎記載。所以說郭紀森是首位提出“衡水人發祥北京琉璃廠”的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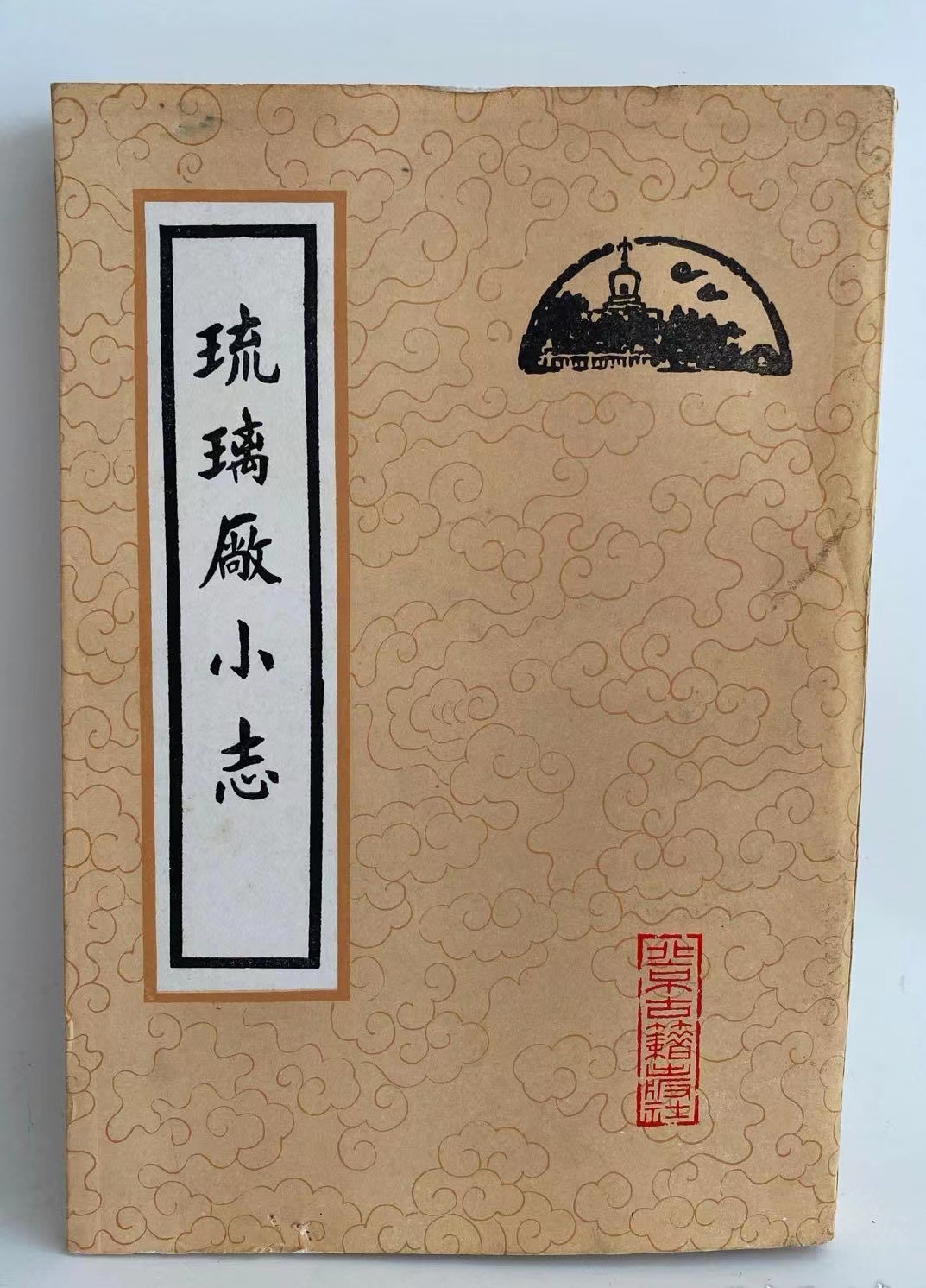
《琉璃廠小志》孫殿起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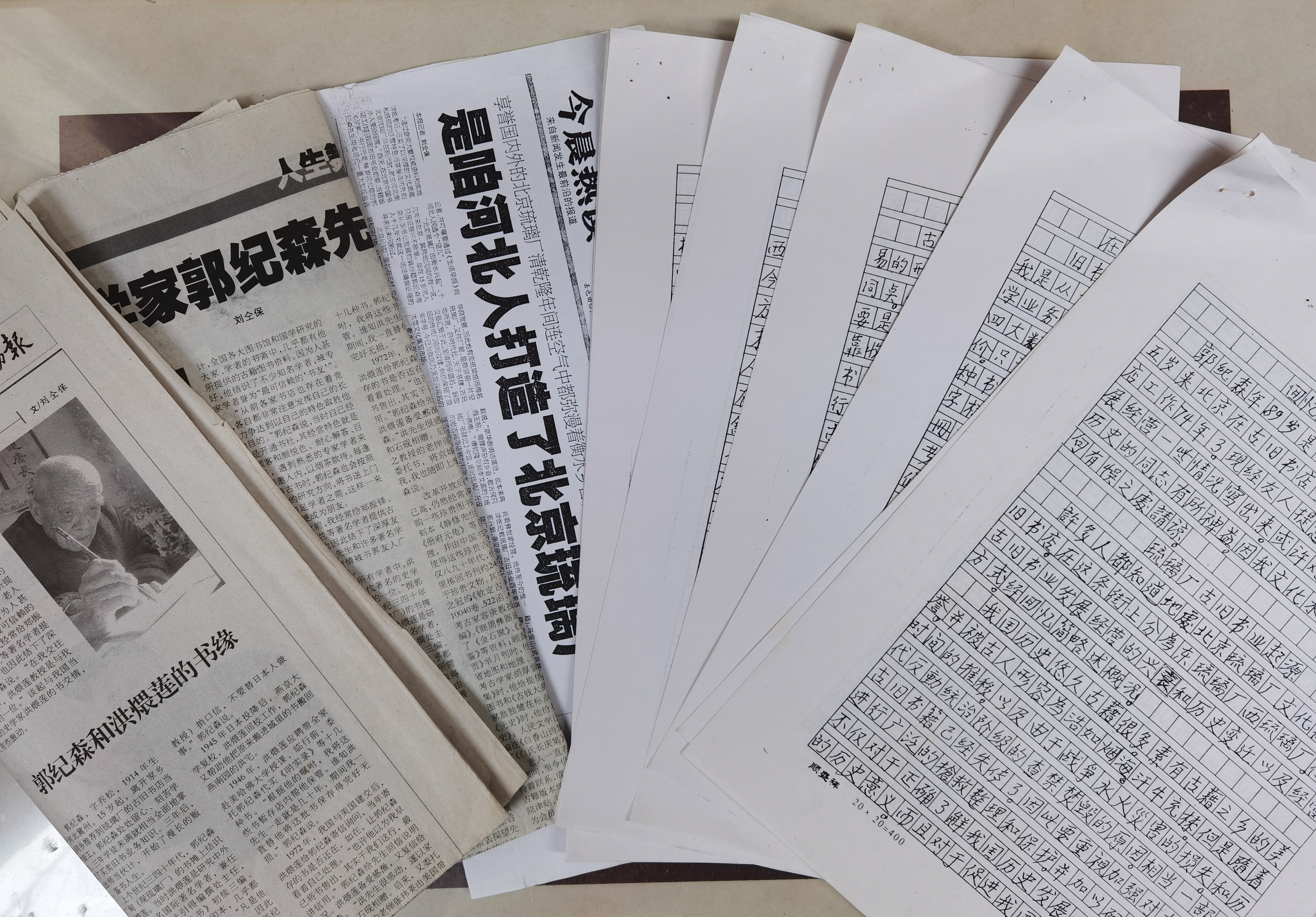
筆者撰寫的琉璃廠衡水人情況的部分報刊資料
很長一段時間內,《人民日報》(海外版)《人民政協報》《中國文化報》《藏書報》《北京晚報》《衡水日報》等都在引用“衡水人發祥北京琉璃廠”這一說法。2001年7月,我在石家莊日報社實習時,通過電話與郭老溝通后再次撰寫《是咱河北人打造了北京琉璃廠》新聞稿,以二版頭條的位置刊發在由石家莊日報社主辦的《生活早報》。郭老說:“這種說法從未間斷過,最近通過查閱大量權威資料和實地詳細考證,足可以確鑿地說是‘衡水人發祥北京琉璃廠’了。”
“衡水人發祥北京琉璃廠”已成文化現象
從城市品牌的角度來看,這是郭紀森及這一學說對家鄉衡水的一大貢獻。從此,衡水、冀州兩級政府及文化傳媒部門紛紛舉起“衡水人發祥北京琉璃廠”這面文化大旗,先后舉辦了一系列活動。其中,冀州在北京舉辦了“北京琉璃廠——追尋冀人的足跡”“中國古舊書文化傳薪者——琉璃廠之冀州人”研討會,聯合媒體深入采訪琉璃廠的冀州人的后人,并編輯整理《琉璃廠之冀州人》專輯。2019年4月,國家博物館館長王春法在北京舉行的“文華衡水”大展前言中寫道:“晚清以降,衡水儒商走京闖衛,促進了北京琉璃廠的文化興盛,培育了眾多行業泰斗與文化耆宿。”筆者在這個由衡水市委市政府主辦的展覽中,看到了對郭紀森等人的介紹,是以“琉璃廠肆”章節進行專題展示,足以說明了他們在北京琉璃廠和衡水儒商中的歷史地位。
另外,在調研中發現衡水有兩個村值得一提,一是冀州大齊村,自清末以來走出了包括著名書畫鑒定家劉九庵和劉光啟等在內的8名文化人;另一是武強縣夾壙村,有5名老藝人在解放后進入榮寶齋工作,如古硯研究專家韓度權、裝裱師韓萬年等。
如今,“衡水人發祥北京琉璃廠”越來越被學術界認可,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民主》雜志主編關永禮、南京大學教授徐雁、鄭州大學圖書館研究員趙長海、原衡水市文化局副局長常海成、冀州市方志辦編輯常來樹等長期將琉璃廠的衡水人作為研究對象,特別是衡水地域文化研究會會長田衛冰挖掘整理的《廠肆衡水幫估史稿》,成為近年來不可多得的系統性的研究成果,極大豐滿了“衡水人發祥北京琉璃廠”學說的意義與內容。他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對“衡水幫”有明確論述:“‘衡水幫’是由衡水縣人肖秉彝開設論古齋而來。‘衡水幫’的地域概念不僅僅是當時衡水縣的區域,甚而也不是今天衡水市十一縣市區的地理區域,‘衡水幫’包括當時的南宮、束鹿、大興、武清等除京師以外貫于直隸全省之人所開設的古玩鋪。”
“衡水人發祥北京琉璃廠”提出至今已有20多年時間,構成了一個地區獨特的文化符號,成為這座城市的人文元素之一,當然也一定會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發展中產生著不可或缺的獨特作用。
琉璃廠文化江山中衡水后繼有人
承續著“衡水人發祥北京琉璃廠”的榮光,我在琉璃廠這條百年老街上穿梭過無數次,拜訪了老先生及他們的后人,從回蕩著的鄉音中還能深深地感知到前輩們的之功之德,也目睹了他們百年之后“子承父業”的輝煌。
2001年11月,吳希賢無疾而終;2009年4月,郭紀森與世長辭;2018年7月,劉金濤辭世。我知道,張宗序、馬春懷、種金明等也都已離世。除了接觸過的這些老先生們,我還從他們口中了解到了另外一些早于他們故去的老先生:古陶瓷鑒定專家孫瀛洲(冀州人)、古舊書人王富晉(冀州人)、王子霖(深州人)、韓斯久(冀州人)、榮寶齋裝裱修復老藝人張貴桐(桃城人)和王家瑞(深州人)等等。
先生們紛紛離去后,琉璃廠也發生了變化,但無論怎么變都少不了衡水人的身影。如今,東西琉璃廠及南新華街上的不少字號里,某些老店的聯營柜臺、合租商鋪中,都不乏衡水人,更有不少老先生的后人依然活躍在父輩們打下的文化江山中,如我一直交往著的馬寶山之子、傳拓技藝代表性傳承人馬國慶,劉金濤之子、中央工藝美術學院裝裱師劉憲懷等等。

劉金濤(后)與齊白石在一起

劉憲懷(左)在裝裱字畫
馬國慶是著名碑帖鑒定家馬寶山老先生的兒子,幾十年來,馬國慶不僅繼承了家學,還在創作中謀求創新。筆者經常與馬國慶泡上一壺茶,聊上大半天,親眼見過他“工作”,大至摩崖碑石,小到甲骨封泥,甚至可以在某件老物件的內壁玩起“盲拓”,用句專業的評價就是“他將高難度的穎拓、造像、浮雕、古墨拓提升到一個新的層次和新的精度。”
劉金濤去世后,次子劉憲懷完全接過了接力棒成為“金濤齋”的新主人。父親的技藝不僅得到了傳承,父輩的友誼同樣延續下來,這就是人們所說的“父一輩、子一輩”吧!他告訴筆者,自己受廖靜文先生之托,曾為徐悲鴻舊作換覆背,近些年還受家屬和弟子之托,為齊白石、祝大年等裝裱遺作。
琉璃廠的衡水人之所以代代相傳,是因為他們身上流淌著一種叫“衡水儒商”的精神。今天,站在新時代談論“衡水人發祥北京琉璃廠”更是衡水人的一種文化自信,意義深遠。
作者:劉仝保 編輯:李耀榮



 廣告
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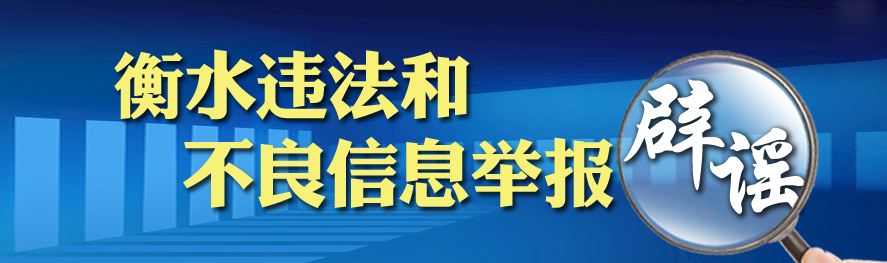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