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口乃鎮江古稱。鎮江至今仍保留有京口區。京口之名,翻譯過來,即京師碼頭。“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從南京到鎮江,城際列車每半小時一趟,區間只需二十分鐘。既便是在交通不便的古代,這里對京城的重要性亦不言而喻。其與瓜洲共處長江和運河的十字交叉線上,軍事鎖鑰,經濟通衢,實乃國家命脈的閘口。清光緒年間,瓜洲作為文學地標中另一處最為著名的古渡,已在洪流沖擊之下坍塌無存,僅剩京口獨峙江岸,如今依舊在唐詩宋詞的流風余韻中顧盼自雄。
京口之行,有人意在金山,在法海、許仙、白娘子。不曉得世間多少人與我有相同的疑問:為什么中國古代傳說里,總喜歡讓善良聰慧的女子愛上一個不諳情事的男人(諸如牛郎、董永、梁山伯,許仙更是一個遇事畏葸、搖擺不定、身不擔當的男人)?是因為這樣的男子尤為憨態可掬?還是為了襯托女子的金堅玉潔?或許從古至今,在愛情里總有一方付出更多,依照慣例,癡情的角色分配給女性更有利于大眾接受與傳播吧。有人則意在登臨北固樓,欄桿拍遍,一抒當年辛稼軒“千古興亡多少事?不盡長江滾滾流”之浩嘆。還有人意在焦山《瘞鶴銘》,想去實地探求中國書法史上意義非凡的“大字之王”的未解之謎。而我,則是為了見證兩場發生在王朝末端、不載于歷史的路過。
此去鎮江,我取道德州,經濟南,過聊城,直奔徐州而行。這一段路程高鐵一直是沿著古老的大運河在走。
道光十九年四月,“因故罰俸”的龔自珍挽舟南下,此時節也正行走在大運河上。因故罰俸之“故”,即是因為他太狂傲,不為時代見容。其實從道光七年開始,他已經戒詩整整十二年了。一名才華蓋世的思想家和詩人,在何等令人窒息的世態里,才可以僅僅為了主人的面子好看,而選擇對自己近乎殘酷的“自宮”。即便如此,在冠蓋如云的京城里廝混了二十年,他才做到正六品的禮部司官,相當于為王府管家的“包衣大”。冷署閑曹,形影相吊,薄俸不足以持家,只能靠典當心愛的藏書艱難度日。“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游。”思想和才華在這里最為廉價,正直的品格只會加重生命的負荷。他已經四十七歲,來到知天命之年的門檻前,終于明白了一個“真理”——狂傲只是別人棄用你的借口!你狂傲他們說你狂傲,你收斂他們依舊嫌棄你不能諂媚。在這個滿目荒蕪沒有生氣的時代,你想敝帚自珍、潔身自好也是萬萬不能的。于是,那就走吧。別了,帝京之城!別了,少年的幻夢!青年的抱負!中年的雄心!
透過蒼茫夜色,我隔窗遠眺古水悠悠的大運河,仿佛在河面上看到一盞微弱但倔強的燈火。在漁燈光不盈尺的照耀里,已經棄絕官場不再戒詩的詩人又一次詩情勃發,胸中塊壘排闥而出,指點江山,抨擊時弊,憂時濟世,面對國脈之艱,民生之苦,一次次淚灑青衫。“不論鹽鐵不籌河,獨倚東南涕淚多。”“我亦曾靡太倉粟,夜聞邪許淚滂沱。”彼年歲次己亥,這一首首涂抹在賬簿紙上丟進竹簏的詩作,后來收編為他著名的《己亥雜詩》。在饑民與纖夫的身影中,他日夜牽念的還有一位老朋友林則徐。三個月前林受命欽差大臣前去南方禁煙。出京之時,他曾呈上一篇《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情辭慷慨地提出禁止鴉片貿易和杜絕白銀漏巵的十項建議。信中除了對林寄托家國厚望,還傾訴了惺惺相惜的摯友深情,表達了自己會相隨南下、共商大計的設想。不料林在給他的回信中委婉勸道,“弟非敢阻止旌旆之南,而事勢有難言者”。萬方多難,國勢衰微,老友此去,身陷政治旋渦,其險惡也是可以想見的。在大運河的槳聲燈影中,他盼望并想象著與朋友南天相聚的美好時刻。
且慢,那一場為中華民族帶來微茫轉機的小聚,也將是他們的訣別,誰能忍心一筆寫盡?讓我們暫行去到金山寺,先來等待崇禎二年的另一場路過。“那管風濤千萬里,妙蓮兩朵是金焦。”金焦二山皆為江中小島,因為長江改道,南岸水位銳減,北岸沖擊力劇增,幾乎在瓜洲沉陷同時,金山與江岸漸漸連為一體。如今游金山寺,不必舍舟登岸,走過長長的山門,而是由一側園門進去徑直到達天王殿前。這樣的游園路線看似只是少走了幾步無關緊要的冤枉路,實則游客們因為沒有時間收攏雜念,故而少有幾分虔敬之心。金山寺始建于東晉,為中國佛教禪宗四大名寺之一。寺院依山而建,山寺錯落,融為一體。穿過天王殿,昂首直見大雄寶殿。我猜想,此處應該就是張岱所記金山夜戲的發生地了。
那年中秋后的第二天,山陰人張岱取道鎮江前往兗州,日暮時分泊船在北固山下的江口。“月光倒囊入水,江濤吞吐,露氣吸之,噀天為白。余大驚喜,移舟過金山寺,已二鼓矣……余呼小仆攜戲具,盛張燈火大殿中,唱韓蘄王金山及長江大戰諸劇。鑼鼓喧填,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采眼翳,翕然張口,呵欠與笑嚏俱至。徐定睛,視為何許人,以何事何時至,皆不敢問。劇完,將曙,解纜過江。山僧至山腳,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張岱由明入清,遁跡山林,凄涼晚景中回首鮮衣怒馬的少年時光,寫下了一篇篇驚為天人的小品文字。明清文人小品讓我們懂得文字的價值,在其真、其善、其美,而非全在政治主旨、宏大敘事和道義承載。
“不信玉門成畏途,欲傾珠海洗邊愁。臨歧極目仍南望,蜃氣連云正結樓。”任何一家王朝到了末期,總要生出幾位試圖力挽狂瀾、偏又時運不濟的志士英豪。這既是個人悲劇,更是王朝崩陷的象征。大明如此,大清也逃不過這個宿命。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出于求和需要,禁煙成功的林則徐從東南沿海發配新疆伊犁,孤身一人踏上了萬里謫戍的征程。這一次路過京口,他決定泊船登岸。因為在這大生死、大抉擇的緊要關頭,他必定會見兩位摯友,懷有無比重要的事情托付。龔自珍自丹陽乘舟,魏源從揚州渡江,在京口一處毫不起眼的小院里,三人促膝而坐,執手晤談。“風清塵不到,潮帶海聲來。”此次聚會三人做出一項重大決策:由林則徐提供資料,由魏源執筆,編寫一本介紹世界的百科全書。林轉眼行期已至,聚散匆匆,江邊揮別,自此青衫飄零,孤蓬萬里。僅僅三個月后,才華橫溢的龔自珍客死丹陽,其壓卷之作恰是兩首懷念故人的《詠史》詩。六個月后,五十卷本《海國圖志》完成最后修訂,不久即刊刻問世。受此影響,晚清啟開了洋務運動的萌芽,日本進入了明治維新時代,東方世界此消彼長的新格局已悄然指向甲午之戰。
繞大雄寶殿后門出來,在熙攘雜沓的游人腳下,在初春和煦的陽光里,藏經樓前忽見一只緊倚欄桿安臥而眠的花貓。它似睡非睡,眼睛半閉半睜,一副享受當下、無關世事的神仙表情。寶殿后墻上寫有五個醒目大字:度一切苦厄。金山下來,我沿江岸向北固山、焦山去。與這兩次鑲嵌在歷史縫隙中的路過一樣,此生我亦路過京口矣。
作者:賈九峰 編輯:李耀榮


 廣告
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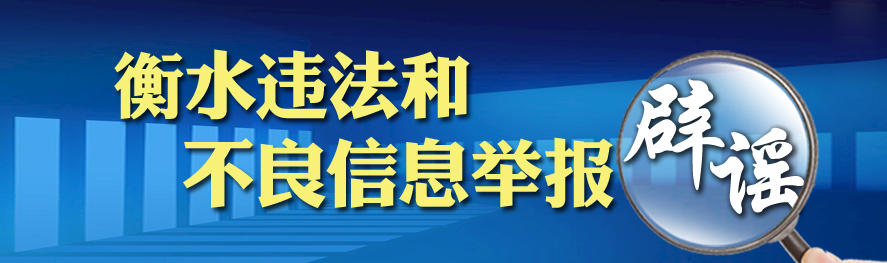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