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吳行盡千山水,猶道桐廬更清美。”2019年初春,我乘車自杭州去千島湖,出錢塘,過富陽,經桐廬,行建德,抵淳安,讀著一路的地名牌,我惘然步入了一幅墨香四溢的詩書畫卷之中。
那年我四十七歲。而在七百年前的延祐二年,四十七歲的黃子久卻被投進了監獄。更為悲催的是,在其入獄之時,熟讀經史的他苦盼幾十年被元廷中斷的科舉制度恢復了。可他身陷囹圄,喪失了報名參考的資格。而他入獄的原因如《錄鬼簿》所記,竟然是“有事論經理田糧,獲直,后在京為權豪所中”。工作中不違背良心,說了幾句真心話,得罪權貴,從而失去了人身自由。三年之后,他刑滿獲釋,求職不成,浪跡杭州,以道袍裹身,賣卜鬻畫為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生五十,顛沛流離,黃子久以一個失敗落拓者的形象一步步來到了富春江邊,斯人大任,天意如此。
明代李日華的《六研齋筆記》如此記錄了他在富春江邊的行為表現。“黃子久終日只在荒山亂石叢木深筱中坐,意態忽忽,人莫測其所為。又居泖中通海處,看激流轟浪,風雨驟至,雖水怪悲詫,亦不顧。”意態忽忽,枯坐亂石,激流成浪,風雨如磐,這既可看作是對山川自然的感悟與體驗,又可理解為道教的苦行修煉。兩者相輔相承,共同促成了他思想方式、生活態度與生命道路的重新選擇。富春江邊,他看似等待,實則是在尋找,在發現。
東漢初年的嚴子陵從釣臺緩緩起身策杖而來。這位漢光武帝劉秀的忘年交本名莊光,后因避漢明帝劉莊名諱,被賜姓嚴(《論語·為政篇》集注云:莊,嚴也)。在長安太學里,嚴子陵身為學長,對孤苦無依的小弟劉秀青眼有加。二人曾同游灞陵,于驛站八角亭中,劉秀面對王莽的一篇辭頌,發出了“我劉家王朝能否中興”的慨嘆,讓嚴子陵相信自己慧眼識人。建武元年,劉秀建立東漢政權,好友嚴子陵竟然在他身邊瞬間消失。他思賢心切,國內發布通告按圖索人,五年后終于有人發現他澤中披裘垂釣,三延而至洛陽。二人同睡,嚴光故意將腳擱置在皇帝的肚皮之上。翌日早朝,便有太史奏告“客星沖犯帝座”。政治之險惡,他直接彩排給皇帝觀看。“早知閑腳無伸處,只合青山臥白云。”他拂衣而去,深藏富春山水。釣臺上一坐千年,石筍西東,溪水潺湲。從此,富春江擁有了自己獨立于天地之間的精神內核。
南朝吳均乘一葉扁舟自富陽溯流而上。“風煙俱凈,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與朱元思書》任意拿出一句,都是山水文字的妙筆。吳均好學有俊才,文體清拔,古氣盎然,開創一代文風,時稱“吳均體”。可南朝幾代,一百六十九年共歷二十四帝,君臣皆有朝不保夕之虞,政治生態極度紊亂,更迭頻仍,動蕩不安。眾多知識分子潔身自愛,只能寄情山水來排遣心中苦悶。“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因為嚴子陵的存在,吳均一管清流選擇了美不勝收的富春江。一封簡短的信箋讓富春山水的美得以千年流傳。
大宋名臣范仲淹以貶謫之身前來睦州,重建破敗不堪的嚴光祠。在《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末尾有名句曰:“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范仲淹對此次修繕極為重視,他在與朋友的通信中多處提及,施工過程力求完美。祠堂落成之時,他專門請來會稽僧人為嚴子陵畫像,親自向大書法家邵疏求字,上述引用的那篇后記他更是盡心運筆,親力親為。嚴先生高風之明燈,在歷經千年之后,又一次被范仲淹的如椽大筆奮然撥亮。從富春江畔,范文忠公一身正氣,文支武絀,逐步走向大宋權力中樞,開啟慶歷新政,試用一己之力挽回日下江河。改良失敗之后,他不戀權柄,斬斷名利,心向江湖,在《岳陽樓記》中一吐“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宏闊誓言。嚴子陵之后,為華夏知識分子樹立起又一座難以企及的精神標高。
在這一枚燈火的指引下,黃子久發現了富春江千年流傳的美妙,找到了富春江自由高蹈的魂魄。他默然從隨身攜帶的布袋里掏出畫筆,而為了這個如此輕巧的動作,他在富春江邊一坐整整三十年。《富春山圖》創稿為元至正七年,此時黃子久八十歲。至正十年竣稿,又三年逝。五十年生活磨礪身心,三十年江邊沉淀靈魂,一千一百八十多個日夜描摹一幅畫作,畫成三年而逝。思接圣賢,往來天地,位居“元四大家”之首的黃公望是用生命創作了如星空北斗般的《富春山圖》。這幅畫的創作可謂奇跡,它后來的命運則更為傳奇。此畫本為師弟鄭樗(號無用上人)所繪,四百年后從民間輾轉入宮,被附庸風雅、以假當真的乾隆帝一題再題,還在畫名中硬塞入一個“居”字,從而產生歧義。因中間有“焚畫殉葬”之故,畫被燒為兩截,各自流傳。如今以《無用師卷》和《剩山圖》分別珍存于臺北故宮博物院和浙江省博物館。
“松柏本孤直,難為桃李顏。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身將客星隱,心與浮云閑。長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按著以詩致敬的體量計算,嚴光大體可以排位在隱逸名士陶淵明之前。唐代詩人中向嚴子陵表達敬意的就達七十多位,知名者如李白、孟浩然、白居易、孟郊、劉長卿、杜牧。更早可追溯到南北朝謝靈運、沈約等人。宋代除范仲淹外,后來致敬者不乏司馬光、王安石、蘇軾、李清照等政治家兼詩詞達人。這些詩詞無不借著對富春山水美景的贊嘆,道出了對嚴先生高風亮節的景仰之情。可翻看以上名人錄,又會發現,他們極少有人舍得如黃子久那樣以生命致敬,最終在名利場中無奈翻滾一生。不知果真見到嚴光先生,他們會是何等心情?
“君因卿相隱,我為名利來。羞見先生面,黃昏過釣臺。”元人趙壁《過釣臺》提醒我,心地雜草未刈,尚無拜見先生的資格。那年初春,我未敢駐車桐廬,貿然晉謁。我期待著自己終有一天再回到富春山水的畫卷之中,于七里瀨的釣臺之上,朝著嚴光披裘垂釣的身影肅然深揖。他的身旁,有范文忠公,有大癡子久。彼時節,江天一碧,猿啼蟬鳴,清風徐來,肺腑若滌。
作者:賈九峰 編輯:李耀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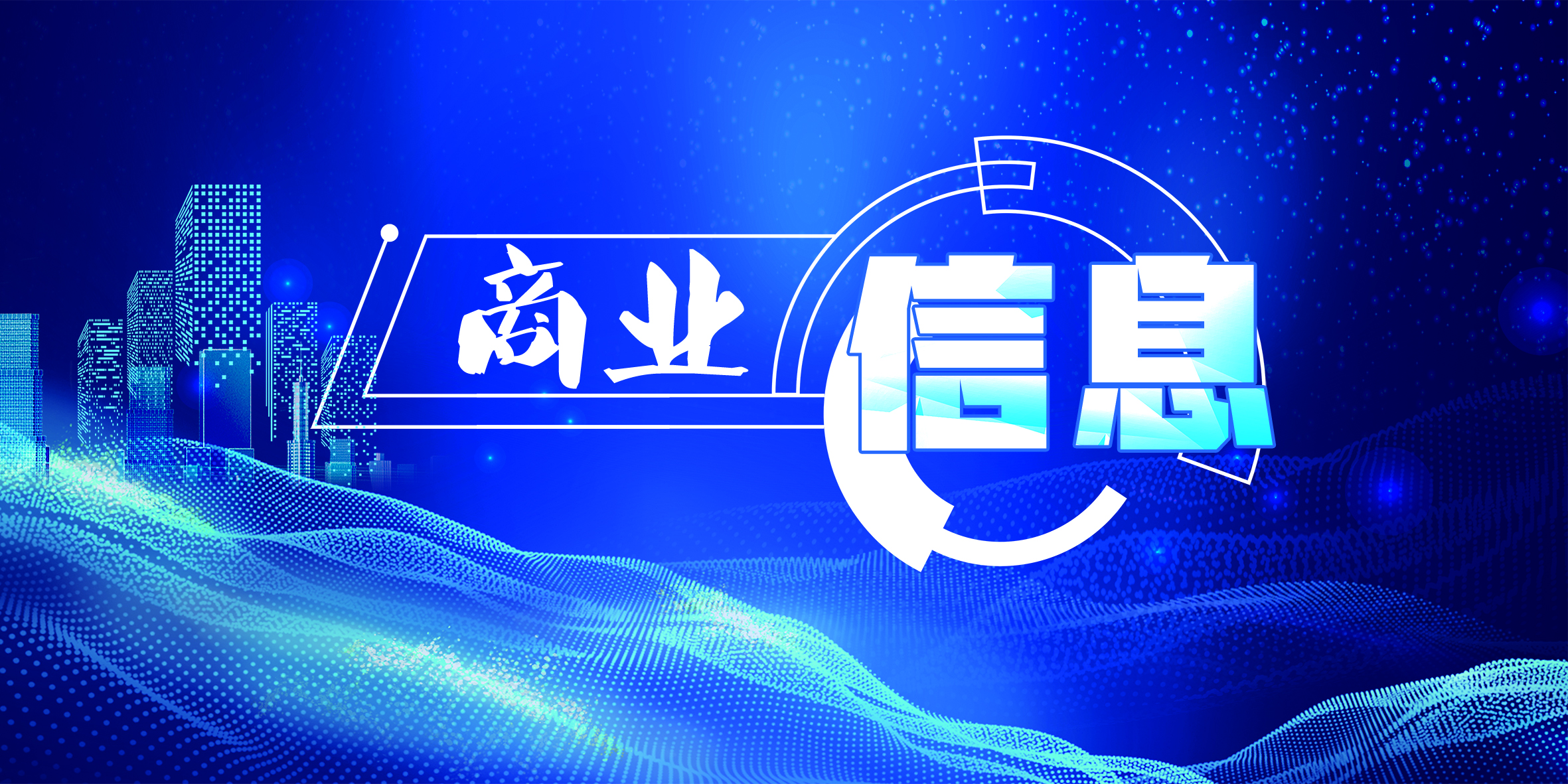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