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走進小學和初中的課堂與孩子們分享童詩時,我發現并非像我們所認為的那樣,孩子的奇思妙想可以瞬間讓他們成為一個小詩人。事實上,在家庭和學校的雙重擠壓下,他們原初的好奇心與想象力正在慢慢被裹挾、吞噬。也就是說,在這個信息不停裂變、飛馳的時代背景中,孩子的輪廓變得越來越模糊,他們身處一個尼爾·波茲曼所說的“一個沒有兒童的時代”,因為他們的童年正在迅速消逝。因此,我時常會這樣問自己:當我們在談論童詩的時候,我們能談論什么?何為童詩?童詩何為?每個孩子真的都是天生的詩人嗎?這些問題其實值得每個童詩創作者思考。

1
在童詩的寫作中,每個人都是自己的迷宮,起源于幼年的語言經驗在我們的身心中已經成為一種魔法。正如卡夫卡所說:“那就是魔法的本質,它不創造,它召喚。”童詩本質上就是召喚,它邀請孩子們進入它的內部,并賦予他們想象的自由和奇跡。詩人諾瓦利斯這樣描述過:“魔法師即詩人。”而孩子與成人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他們還堅信魔法的存在。
什么是童詩?談論這個看似很小的問題令我感到不安,寫作童詩是艱難的,談論童詩更難。因為你要談的是一種正在流動和變化的神秘的語調和聲音,如同你在談論神靈的語言。那些初始的愛、記憶與心靈狀態一下子將我們帶至純真和想象的融會中。這時,我通常喜歡引用英國作家依尼諾·法吉恩的一首童詩作為回答:
《什么是詩》
什么是詩?誰知道?
玫瑰不是詩,玫瑰的香氣才是詩;
天空不是詩,天光才是詩;
蒼蠅不是詩,蒼蠅身上的亮閃才是詩;
海不是詩,海的喘息才是詩;
我不是詩,那使得我
看見聽到感知某些散文無法表達的意味的語言才是詩;
但是什么是詩?誰知道?
這里,詩歌作為一種永遠無法抵達的力量出現在我們的認知中,從而建立起世間萬物的隱秘關聯,在這一“未知”中,兒童心靈的回歸變得尤為重要。比如在日本詩人金子美玲的童謠中花香就是花朵的呼吸,法國作家圣埃克蘇佩里描繪的花朵是星球的詩意綻放,奧地利詩人漢斯·雅尼什會把掌聲獻給一束花,而七歲的孩子小二牛在詩中說花是佛的手指。童詩成了語言的游戲之夢,它是想象與魔法的勝利。童詩的藝術在于發現心靈的自由、萬物的奇妙以及對情感、生命乃至宇宙的挖掘,從而發現自我,走向內心。

當然,每個詩人和讀者對于童詩的認知都不同,這也是童詩存在的意義,當童詩來臨的時候,你會發現你的世界在生花、在結籽、在閃光。比如,在孩子心中寫詩就像拍蚊子:
《詩是什么》
作者:李雨融(7歲)
寫詩有點像拍蚊子
有時候我一不小心
就按死一個
有時候
我拼命地拍打
卻怎么也打不到它
我覺得寫詩
就是這樣
事實上,談論童詩的概念本身似乎并無太大意義,童詩永遠只是探尋而非抵達。對兒童而言,通過詩歌帶來的感覺而非意義、概念和方法,更能讓他們體會語言之美,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孕育而生的。
時間退回到2019年,我第一次做面向全國的童詩網課,那些最柔軟、最圣潔的幼小的靈魂讓我見證了一個“永恒的時刻”。孩子和家長的心靈合成的花束如同“語言的贊歌”深深觸動著我。從那時起,史蒂文森的幻想、希爾弗斯坦的荒誕、羅大里的反諷、特德·休斯的狂野、金子美鈴的哀傷、窗道雄的憐惜、顧城的純潔……都為孩子們提供了豐富、明亮的語言水晶。于是,一直以來,童詩在普通讀者的認知中的“小兒科”、“淺語”、“模仿孩子說話”、“想象的玩意”等符號瞬間變得微不足道。在優秀的詩人作品中,你會發現,好的童詩不光是兒童心靈的藝術,同時也能給成人帶來純潔的體驗,就像“小王子”所說:“每個大人都是曾經的孩童,雖然只有少數人記得。”而那些“少數人”也在和孩子們一起編織著童詩的迷宮夢。

隨著孩子的寫作和鑒賞力的不斷深入,他們對語言的體驗也會像命運一樣展開,所以并非像一般人認為的那樣,孩子對童詩的認知與成人有明顯的界限,如果有,也是因為孩子內心更敏銳、純潔,作為獨立的個體,就像加拿大李利安·H·史密斯在《歡欣歲月》中的提示:“刻意給他們只有韻律和節奏的作品反倒無用;將他們年幼卻蓬勃的想象力用那些故意顯得簡單、淺顯的作品限制起來則是狹隘的。在閱讀詩歌的時候,兒童的想象力總是可以超越他的理解能力的,他的情緒將帶他越過其心智上的限制……”“通過直覺與想象,兒童能理解那些遠遠超過他們經驗限制的東西”。這時我更愿意分享一些我童詩課的孩子的作品來呈現語言的世界:
《融化在月光里》
作者:橙子(6歲)
穿著花裙的白兔
提著光
站在發著微光的彩虹花瓣上
輕輕的,拍打著時光的窗
邀請我
看月光舞蹈
我的心
輕輕的,飄了起來
融化在
月光里

2
“提著光”是一種怎樣的體驗?孩子的自我的想象與經驗難道僅僅只是語言的夢幻?這些看似靈光乍現的詩句,其實有著清晰的內在邏輯。童詩變成了夢幻之物:
《帶一只羊駝去看梵高的<星空>》
作者:姜雨琦(7歲)
有一天我找到了羊駝
他問我從哪里來
我說我從梵高的畫里來
他說梵高的畫里沒有羊駝
你怎么學會羊駝的語言的?
我說梵高的畫里有星空
我在羊駝星上學會了羊駝的語言
羊駝眼里閃著淚花
他問我可以帶它去看那幅畫嗎?
我說咱們快走吧
羊駝女王派我來找你
你到了那幅畫面前
她就施魔法把你變回羊駝星球
你就可以回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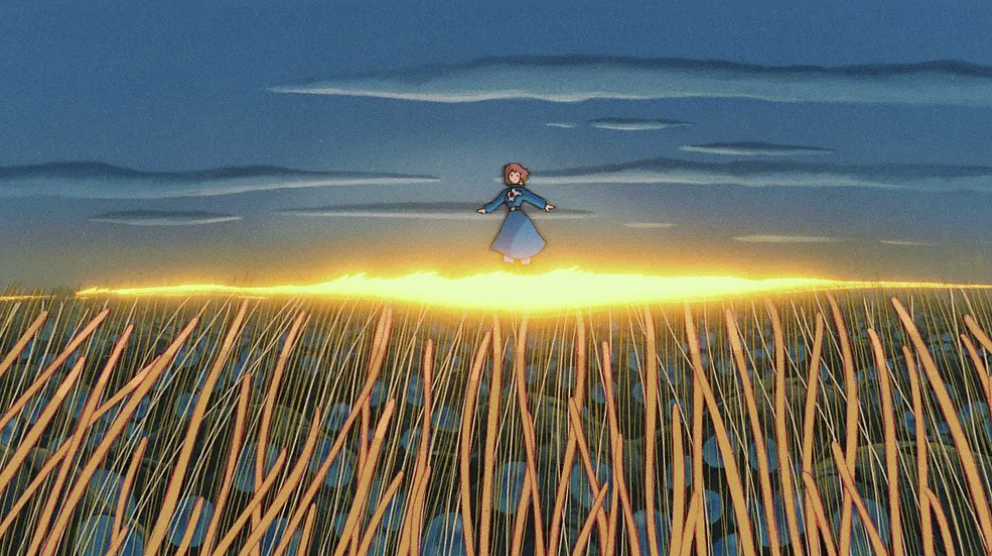
看吧,孩子對事物的理解絕非我們想象的那么簡單,“為兒童”寫作的傲慢其實是成人經驗的誤讀,漢斯·雅尼什說:“優秀的童詩能讓讀者心中明朗,獲得慰藉;能夠觸動人的心靈,溫暖每個孤單的靈魂。一首優秀的童詩應該講述對人、對物的愛,發人深省,讓讀者去感受,去大笑。”于是孩子們又開始這樣描繪他們看見的世界:
《暴紙》
作者:哈哈(5歲)
有時候抽紙的脾氣很暴躁
晚上睡覺的時候他會躲在袋子里
所以我要叫他“暴紙”
報紙的脾氣也很暴躁
被人輕輕碰一下撕一下就爛了
抽紙的脾氣很暴躁
報紙的脾氣也很暴躁
可是都叫他們“暴紙”也不行
我們得想個辦法
《死亡》
作者:顧惜語(10歲)
死亡之神
在頭頂盤旋
一瞬間
靈魂飛升
身體輕盈
像紙一樣
穿過金色的麥田
飛越藍色的海洋
輕撫柔軟的白云
時間的指針已被風
溫柔地折斷

《時間王國》
作者:朱莉雅(10歲)
在離地球三百六十五條
狐貍尾巴遠的地方
有一個小小
玻璃球一樣的
時間王國
王國上
生活著九十九個
時間小人
藍菊花瓣的花心里
坐著藍色皮膚的
時間國王
它們都很小
從花苞到落葉
也沒有人能看到
這是一個秘密
太陽告訴月亮時
被路過的風吃進了肚子里
你很難想象這些詩句是出自不同年齡的孩子的心靈,沿著他們語言的軌跡,你會發現許多有趣的靈魂、愛、疑問與思考的路線圖。
優秀的童詩無時無刻不在拓寬一種新的童詩美學,它必須是“詩的藝術”,它向我們宣告若不借助想象的翅膀,語言便無法抵達更遠的未來。童詩的生命力、奇妙之夢與想象的宇宙,一切的詩性都指向語言的未來:
《星月的來由》
作者:顧城(12歲)
樹枝想去撕裂天空,
但卻只戳了幾個微小的窟窿,
它透出天外的光亮,
人們把它叫做月亮和星星。
多么美麗的童年力量,它的棱鏡折射出的語言藝術正是迷宮的入口。同樣是12歲,留守兒童杭建對星空的夢幻同樣具有神秘的圖景:“你瞧,樹枝在畫畫/星星和月亮/是它筆頭上的光。”(《畫畫》,懷遠縣龍祥小學)。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我們被童詩的語言藝術所吸引,我們就如同置身于迷宮中,那些隱藏在事物中的美好都會被發現和洞悉,進而引領我們重返生命的最初時刻。當然,我們也無法忘記西班牙詩人洛爾迦的那首關于樹木的詩:“樹啊/你們可是/從藍天射下來的箭/多么可怕的武士才能/挽這樣的弓/難道是星星?”詩人在尋覓遙遠的回應時,也給我們帶來陌生的奇特體驗,童詩本身不就是我們整個身心的宇宙嗎?

3
現代的孩子接觸的事物越來越廣闊,以往占主導地位的鄉村題材的童詩逐漸與當下的兒童拉開了距離。也就是說,原來納入到童詩審美范疇的那些處理對象,已經開始失效。在童詩的演化過程中,我們需要構建的審美對象也變得越來越豐富,除了兒童,成人(尤其家長)也加入到閱讀童詩的序列中,這為童詩的寫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法國作家菲力普·阿力埃斯在其著作《兒童的世紀:舊制度下的兒童和家庭生活》中提到“發現兒童”這一重要的觀點。他說:“發現幼童,即發現幼童的身體,發現幼童的姿態,發現幼童的童言稚語。”優秀的童詩需要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前進,我們只有發現并正視兒童的語言,相信兒童想象的力量,相信他們的心靈與奇跡,才能真正走向童詩未來的迷宮夢。
編輯:李耀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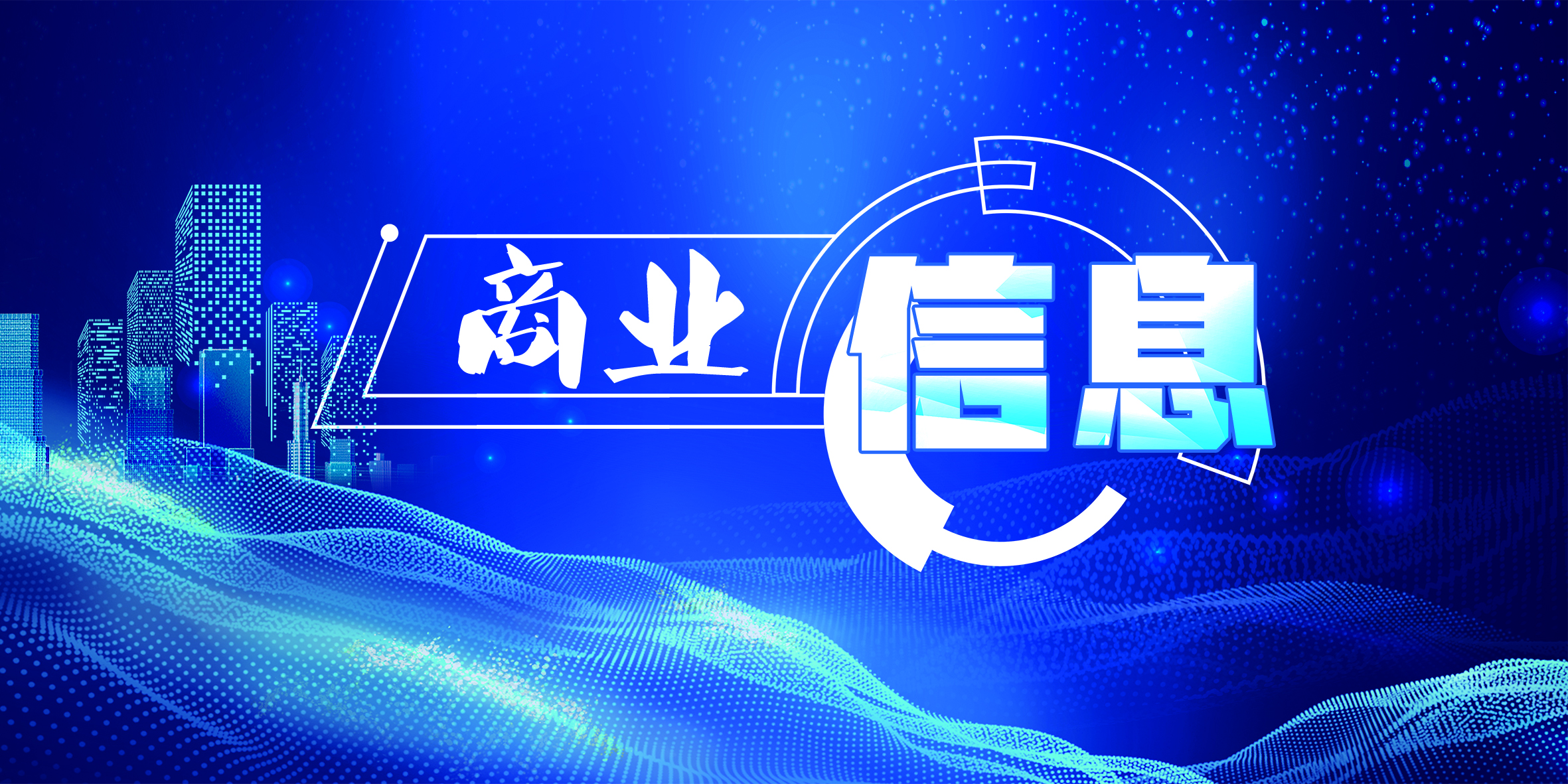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