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豐三年正月初一,驚魂未定的蘇軾步出牢門,逃也似的離了東京汴梁。這一日,朔風凜冽,彤云欲雪。
在這位即將到任的黃州團練副使身后,竟無一人相送。那些欲將他置之死地的朋友們,此時朝賀已畢,歸至家中,正燕樂作舞,依翠偎紅。蘇軾的委任狀上還附有兩個條款:一不得披閱文件,二不得隨意出入黃州。這分明是一個無職無權、身受監管的朝廷犯官。只是他卻不知,這條貶謫之路,始于絕獄,終于絕壁。從絕獄到絕壁,他或是毀滅,或是涅槃重生。
絕獄指烏臺詩案。《漢書》載:“其府(御史臺)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這是御史臺始稱烏臺的來歷。蘇軾一生宦海沉浮,仕途坎壈,但真正身陷囹圄遭受到死亡威脅的僅此一次。元豐二年四月,蘇軾自徐州調任湖州知州,二十日到任后進《湖州謝上表》。秋七月,即因上表中的“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一句,遭到御史臺官員何正臣、李定、舒亶連續奏章彈劾,奏其“攻擊新法,諷刺朝政”。神宗大為惱火,遂批示將其逮捕下獄。八月十八日入獄,二十日正式提審。此時除了舒亶、李定等群小的圍攻,又跳出國子博士李宜之、《夢溪筆談》著者沈括等人,從蘇軾的書信詩文中尋章摘句,急欲置其于死地。蘇軾與長子蘇邁暗中約定,平時只送菜飯,如有死刑判決的消息就改送魚,以便心里早做準備。某日蘇邁出京借錢,將送飯一事托人代勞。該人不知密約,特備熏魚以進。蘇軾大驚,自知兇多吉少,極度悲傷之際,為弟子由寫下訣別詩:“柏臺霜氣夜凄凄,風動瑯珰月向低。夢繞云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歲神游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事后雖知是一場虛驚,但相信那漫長一夜他已洞見了生死之門。
我所讀知最早記載的文字獄發生在漢宣帝時代。士大夫楊惲,其父為丞相楊敞,外祖父更是大名鼎鼎的史學家司馬遷。楊惲重義輕財,嫉惡如仇,杜絕行賄,任職清廉。由此得罪太仆戴長樂,被告以“以主上為戲,語近悖逆”,自此削去爵位,免為庶民。其后歸家治產,飲酒田園,以財為樂。在楊惲《報孫會宗書》中有歌云:“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就是這樣與世無爭的幾句話,又被人呈報給漢宣帝,以大逆不道之罪,處以腰斬。
我猜想,最終讓神宗做出刀下留人放蘇軾一條活路的原因,除了太祖有“不得濫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之人”的碑文密誓,更為重要的是神宗在那些小人的彈劾詞中,嗅出了瘋狗亂咬、不近情理的味道。例如狀告蘇軾“初學無術,濫得時名”,“急于獲得高位,心中不滿之下,乃譏訕權要”等,這無形之中助抬了神宗的圣手,在大理寺與審刑院做出的“當徒二年,會赦當原”的判決書上揮筆圈定。
元豐三年二月,蘇軾初至黃州,寓居定惠院。定惠院是一座不大的寺院,坐落在一處距江邊不遠林木茂密的山坡上。他與僧人一道吃飯,然后在誦經聲里繼續咀嚼人生。這無疑為蘇軾在儒學之外深入求佛問道提供了一個契機。如果說原來佛老之學在蘇軾的學養之中屬于增彩花色,那么此番歷經生死考驗之后,他主動從“具體的政治憂患轉而為寬廣的人生憂患”,佛經道藏已然登堂入室,成為其生命給養的正牌大餐。元豐四年,老朋友馬正卿可憐他乏食挨餓,“于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此地位于黃州城東,踞于山坡,故名東坡,由是他自稱“東坡居士”。三年之中,他寫《臨江仙》《黃州安國寺記》《寒食帖》《東坡八首》《黃泥坂詞》等詩文,都是以居士之心,為了走向人生中那一道絕壁做著靈魂上的準備。元豐五年七月既望之夜,那個心智已然成熟的蘇東坡終于來了。
這是文化、哲學、藝術及思想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游歷。一葉葦舟,凌波萬頃,但見斷岸高聳,壁立千仞,橫絕無路。于是“客有吹洞簫者……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余音裊裊,不絕如縷。”“何為其然也?”“你還記得發生在赤壁的往事嗎?你還記得曹操寫下的詩句嗎?這些蓋世英雄如今在哪里呢?今夜你和我,一杯在手,享一時之樂,可在天地之間,我們的生命短暫如蜉蝣,渺小如砂粒,生死須臾,而明月永在,江水無窮,這難道不令人悲傷嗎?”對于每一個有過生命思考的人,死亡都是一道無法繞過的命題。越是有質量的生命,越容易陷入“吾生也有涯”的驚懼與憂傷。并非每個生命都能達到這個層次,從而獲取憂懼的資本。此夜此時,死亡以赤壁的形象屹立在蘇東坡的面前,向他討要一個回答——“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天地之間,萬物各有歸屬,若不該我們擁有,即令一絲一毫也求取不來。只有江上清風,山間明月,耳得之為聲,目遇之成色,這正是造物者賜予我們盡情享用的無盡寶藏啊!”變與不變,深奧精微的哲學問題,千年之前能夠從變與不變兩個角度、運用辯證思維去看待世界(包括生命),明顯已經超越了悲觀的死亡終結論調,升華到“物與我皆無盡”的永恒空間,此為蘇東坡過人之處。而這個看似信口道出的超越,在屈原、李白的詩歌里,還屬于缺乏理論支撐的、夢求囈語般的浪漫情懷。在蘇東坡之前,沒有人能將其闡述得如此明晰。在蘇東坡之后,亦很少有人能將其味入命運的寫作之中。縱觀古今中外浩如煙海的生命哲學文字,這一段《赤壁賦》依舊是無人逾越的高峰。
諸多文學史家持相同的觀點:黃州赤壁非真赤壁,因蘇軾而留名。此言謬矣。來到黃州,先有東坡耕耘,始有東坡居士。到得赤壁,絕地轉寰,超拔而歸,才開創出人生雄闊大境。在烏臺,他看透了生。在赤壁,他悟出了死。其后,“自喜漸不為人識”的他生命進入自由狀態,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佳句迭出,名篇天成。應該說正是黃州赤壁成就了他,從優秀的文學家蘇軾活出了偉大的文學家蘇東坡。真假赤壁,還重要嗎?這注定是蘇子的赤壁,是一面高聳于天地之間的文化、哲學、藝術、思想的豐碑。
作者:賈九峰 編輯:李耀榮
 廣告
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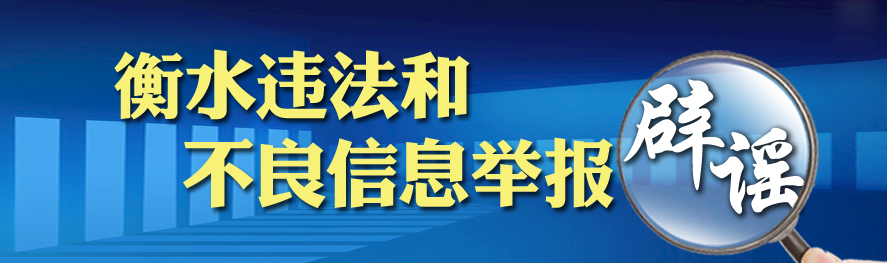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