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識依利米努爾·艾麥爾江,是在央視綜合頻道一個經典詩詞詠唱的節目里。模樣俊俏的小姑娘,來自新疆且末縣的大山“那一邊”——塔克拉瑪干沙漠的東南緣、阿爾金山的北麓。
且末縣的歷史悠久,西漢張騫出使西域時,第一次將且末古國的情況帶回內地;唐玄奘自印度取經回來,也曾經過這里,《大唐西域記》里對且末有記載……
依利米努爾朗誦的是作家王家新著名的新詩《在山的那邊》。她用動聽的童聲,詮釋了一個耽于幻想、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好奇心少年的美好愿望:
“小時候,我常伏在窗口癡想:
山那邊是什么呢?
媽媽給我說過:海。
哦,山那邊是海嗎?
于是,懷著一種隱秘的想望,
有一天我終于爬上了那個山頂。
可是,我卻幾乎是哭著回來了:
在山的那邊,依然是山,
山那邊的山啊,鐵青著臉,
給我的幻想打了一個零分!
媽媽,那個海呢?”
主持人好奇地詢問依利米努爾,你為什么自稱“小紅柳”呢?小姑娘忽閃著大眼睛:“紅柳樹能在極度干旱、沒有水的沙漠里生長,生命力很強,所以在沙漠里長大的孩子,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小紅柳’”。小姑娘還說,她之所以能從且末走到烏魯木齊,又從烏魯木齊走到北京中央電視臺,是因為有一個好老師李桂枝的培養支持。李老師2000年從河北保定師范畢業,來且末支教,就像一株紅柳樹一樣,扎根在這塔克拉瑪干沙漠了……
“小紅柳”揮了一下拳頭:我這次雖然沒有能“晉級”,但我會繼續努力的,就像《在山的那邊》的詩里講的:
“在山的那邊,是海!
是用信念凝成的海……”
“小紅柳”的故事讓我感動,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并且它還引發起我對尋找紅柳樹的深刻記憶。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從報紙上看到關于紅柳樹的報道,知道它是一種不尋常的樹,是沙漠和高原上最美的樹。于是對紅柳產生了一種崇拜、熱愛的沖動,盼望有一天能親眼看一看、摸一摸這“偉大”的紅柳樹。
第一次機會出現在2003年夏天。那次雖然到了新疆石河子、吐魯番,但沒有尋找到紅柳。聽當地人講,塔里木盆地周邊的沙漠地到處都有紅柳樹。由于任務緊急,只好怏怏而歸。人常說,愈是找不到、看不到的東西,就愈想找到它、看到它。我從資料上了解到:紅柳樹,又名桑樹柳,是一種灌木,最高能長到兩米多。它的莖稈為棗紅色,墨綠色的葉子非常瘦小,屬于鱗片葉,一般在春夏之交開花,花為粉紅色。它能在高原、鹽堿地、戈壁荒灘等貧瘠的土壤里生長,能頂風冒雪、防風固沙,具有很強的生命力……
2007年9月,我有幸再次赴新疆出差,這次到了塔克拉瑪干沙漠的西緣。據當地人說,塔克拉瑪干的意思是“進得去出不來”。9月21日上午,我們從古絲綢之路上的璀璨明珠——喀什出發,去地處沙漠邊緣的岳普湖縣,在路經疏勒縣時遇到大片紅柳樹。我“強烈”要求司機在路邊停車。
難道這就是我朝思暮想的“絢爛、紅艷、茂盛、如熊熊燃燒的烈火般的紅柳樹嗎?”其實,它就像家鄉根治海河前鹽堿洼地里的灌木“紅荊”一般,一人多高,開著粉紅色的花。只不過紅柳的莖稈韌性更強,細的可以用來編筐,粗的可以當筐框,還可做農民平整土地的耙子……
回到烏魯木齊,曾在中央黨校一起學習的同學劉剛來看望。我興奮地向他報告:“在疏勒和岳普湖縣我看到紅柳了!”沒想到他哈哈大笑,那笑聲中似乎有一種“少見多怪”的意思,讓我有些不解。細談起來,才了解到,原來他祖籍安徽,父親隨一野部隊進疆,離休前曾任新疆建設兵團副政委。劉剛是建設兵團的第二代,1951年出生在烏魯木齊。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他親自經歷了建設兵團建設“兩圈一線”的戰天斗地的可歌可泣的戰斗歷程。
所謂“兩圈”,是指圍繞塔里木盆地和準格爾盆地靠近沙漠的兩個“大圈”周邊,大力種植能夠在戈壁荒漠殘酷環境生長、并能防風固沙的紅柳。而“一線”則指的是守衛邊疆、建設邊疆、扎根邊境。劉剛還說,我去的疏勒縣和岳普湖縣,是建設兵團的農三師的駐防地,是當年他們種植紅柳的地方。紅柳雖沒有松柏的偉岸,但它以特有的能忍耐、能吃苦、能抗爭、能奉獻的品格,在戈壁荒漠中頑強地成長,像軍墾戰士一樣守護著祖國的邊疆。
一席話說得我茅塞頓開。望著劉剛黑黝黝的面孔,我不由得肅然起敬:紅色是最美的顏色,紅柳是最神圣的樹。而劉剛不也是一株紅柳嗎?只不過這當年的“小紅柳”,隨著歲月的消磨和生活的跋涉磨煉成了“老紅柳”——一名德才兼備的兵團中層干部了!
作者:張錫杰 編輯:李耀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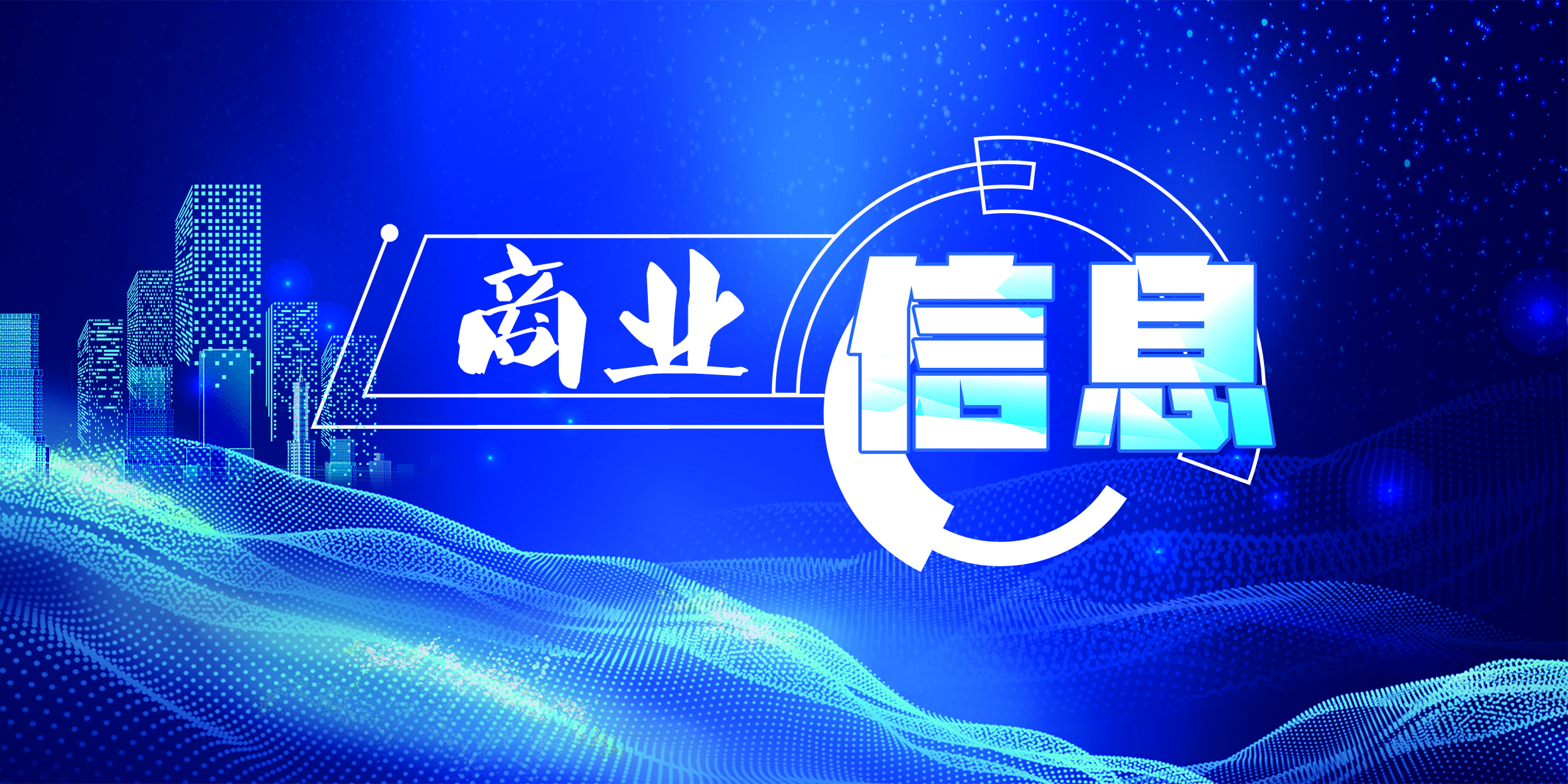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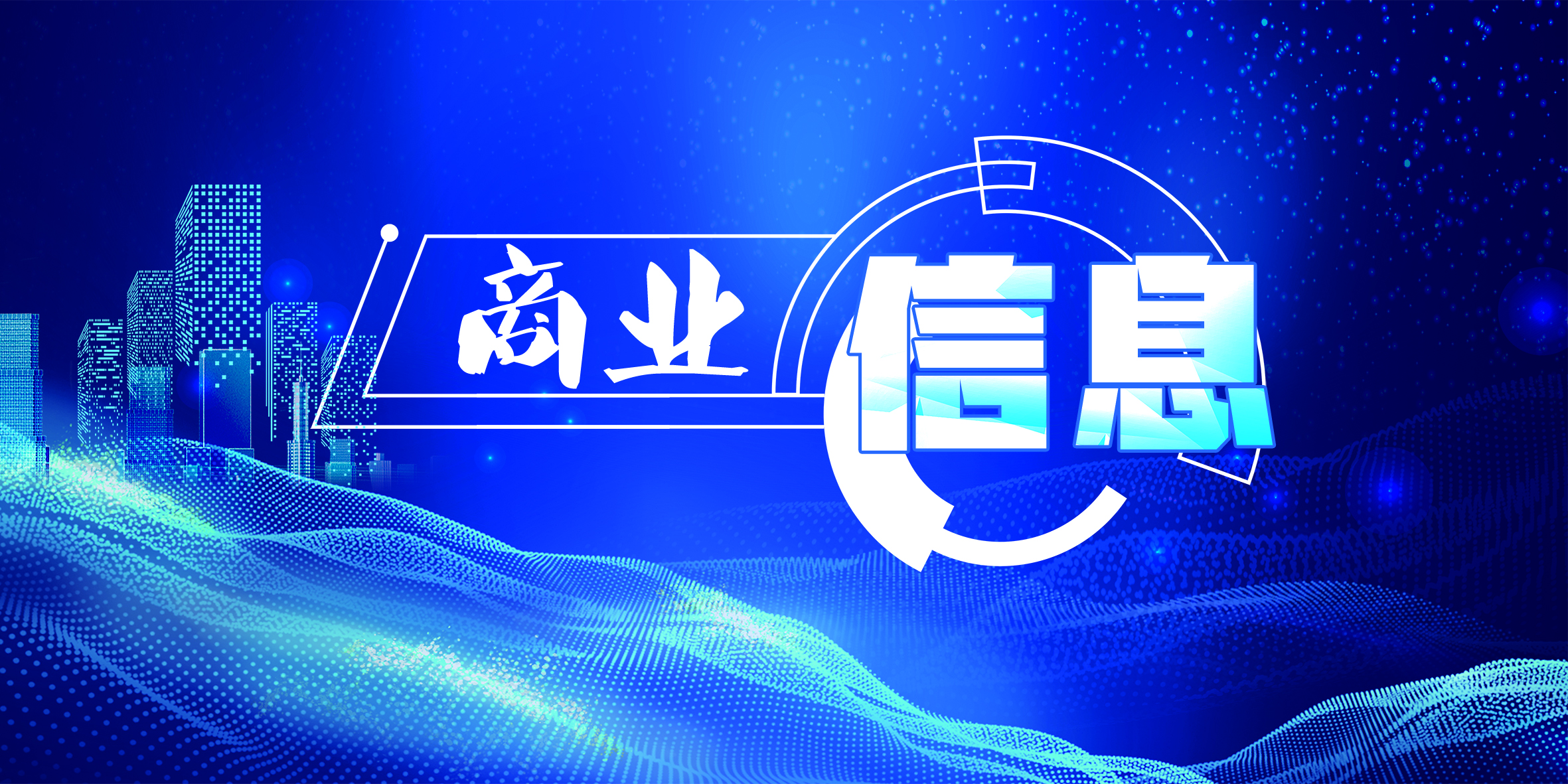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