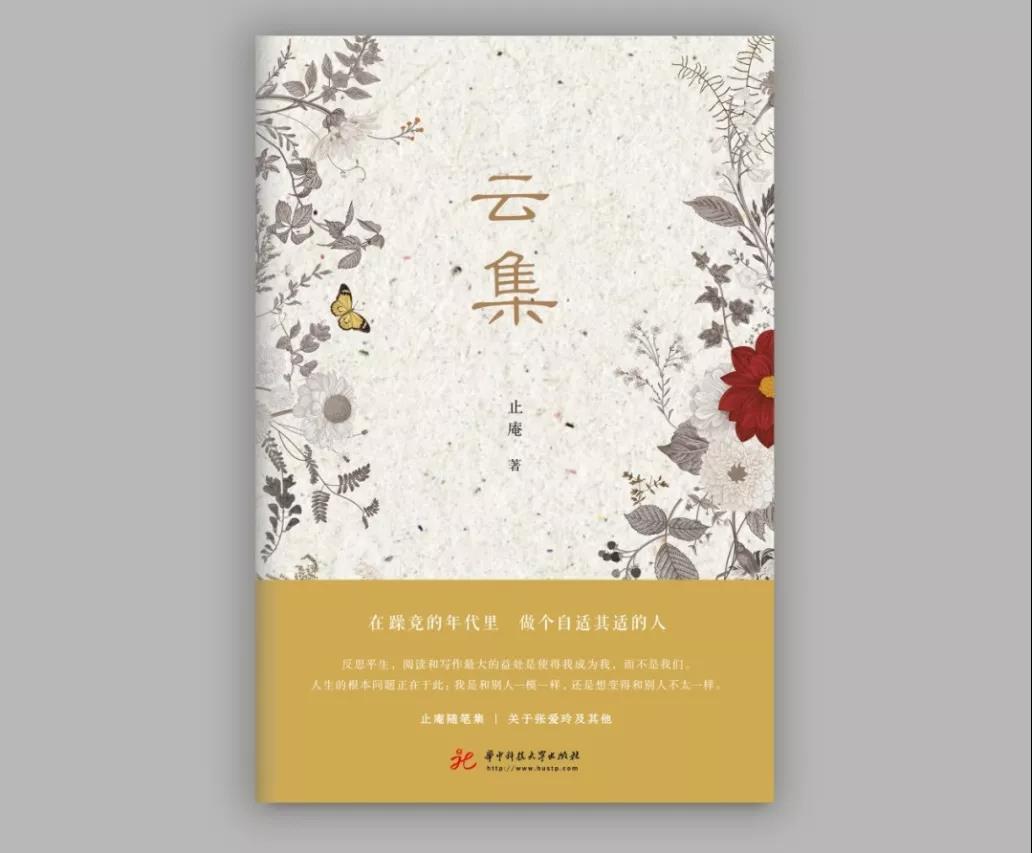
止庵《云集》| 關(guān)于張愛(ài)玲及其他
華中科技大學(xué)出版社 2020
和一般的讀書(shū)隨筆不同,讀止庵的《云集》,從來(lái)不是讀常識(shí),他對(duì)大家已知的知識(shí)通常一帶而過(guò),很少展開(kāi)來(lái)講。
讀他的隨筆集,讀的是態(tài)度。
他對(duì)文學(xué)的態(tài)度,更多的是對(duì)人的興趣,他讀作品,是為了解作者,了解自己,了解人的普遍性。
他在序言中寫(xiě)道:“我們盡管活在當(dāng)下,但與過(guò)去還是有千絲萬(wàn)縷的聯(lián)系,我們的孤獨(dú),惆悵,悲痛,快樂(lè),正與過(guò)去的人的某一時(shí)刻相去不遠(yuǎn),彼此能找到心靈相通的地方。”
“孔子活在距離現(xiàn)在兩千多年前的年代,我們回過(guò)頭去,還是能看見(jiàn)這些遙遠(yuǎn)的人,因?yàn)樗麄兤鋵?shí)是與我們相同的人,對(duì)人生和世界具有類似的感受和認(rèn)識(shí),所以才能產(chǎn)生共鳴。也許只是相視一笑或一泣,甚至相對(duì)無(wú)言,然而卻惺惺相惜,心心相印。”
這也是止庵花費(fèi)一生大部分精力用于讀書(shū)的原由:盡量結(jié)識(shí)古今中外的智者,了解他們的感受,想法。潛心去聽(tīng)遠(yuǎn)方傳來(lái)的呼應(yīng)。
止庵曾講過(guò),讀書(shū),于他是一種必要的自我教育,可以補(bǔ)學(xué)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huì)教育之不足。正因如此,《云集》實(shí)為作者自我教育過(guò)程的一份記錄,寫(xiě)來(lái)寫(xiě)去,最終觀照的并不是所談?wù)摰淖髡吆妥髌罚钦務(wù)撜咦约骸?nbsp;

止庵
作家,學(xué)者。視讀書(shū)為自我教育的一條途徑。
出版有《惜別》《畫(huà)見(jiàn)》《游日記》《如面談》《樗下隨筆》等著作,
并編訂周作人、張愛(ài)玲作品。
《云集》由“收螢卷”和“傳奇人物圖贊”兩個(gè)部分集成。前部分是隨筆文章,后部分是張愛(ài)玲小說(shuō)人物專談,這也是迄今為止止庵寫(xiě)張愛(ài)玲最完整的集子。
其中“收螢卷”集文三十二篇,開(kāi)篇還是從止庵熟悉的領(lǐng)域周氏兄弟談起,另外還有外國(guó)文學(xué),如阿爾志跋綏夫、普里什文、納博科夫、卡爾維諾、帕慕克等。
另一部分“傳奇人物圖贊”,依次談?wù)搹垚?ài)玲的《茉莉香片》《心經(jīng)》《傾城之戀》《琉璃瓦》《金鎖記》《年青的時(shí)候》《花凋》《紅玫瑰與白玫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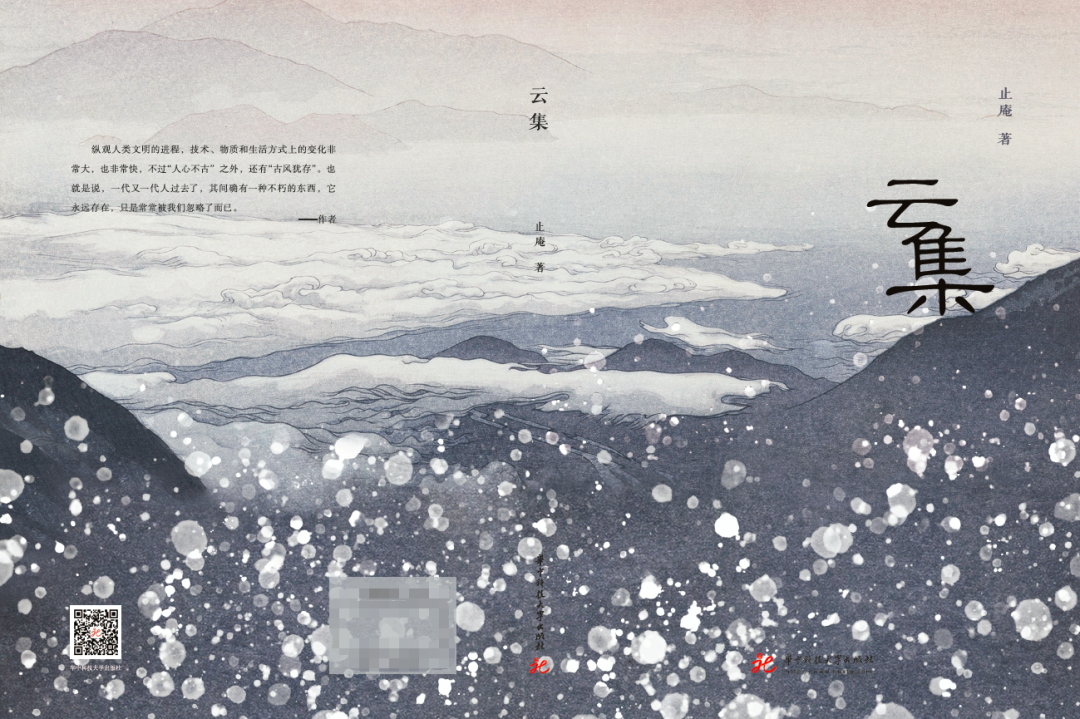
《云集》最初的封面,意象是“云”。
但打樣效果并不理想,于是重新打磨封面。
從張愛(ài)玲著手,由 “花”這個(gè)角度切入。
止庵談張愛(ài)玲
張愛(ài)玲筆下存在著兩個(gè)視點(diǎn),一是人間視點(diǎn);一是在此之上,俯看整個(gè)人間的視點(diǎn)。從前者出發(fā),人物自有其人生的愿望與體驗(yàn);從后者出發(fā),這些愿望與體驗(yàn)是何其微不足道。
《色,戒》是張愛(ài)玲描寫(xiě)人的情感——不僅僅是愛(ài)情——最復(fù)雜、最深刻的一篇小說(shuō),不易理解,甚至常被誤解。
假如張愛(ài)玲文學(xué)中有“張愛(ài)玲哲學(xué)”的話,概括起來(lái)就是《傾城之戀》所說(shuō):“在這動(dòng)蕩的世界里,錢財(cái),地產(chǎn),天長(zhǎng)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這口氣,還有睡在她身邊的這個(gè)人。”
張愛(ài)玲的小說(shuō)布局精巧,構(gòu)思嚴(yán)謹(jǐn),任你如何推敲,總歸滴水不漏。而她駕馭語(yǔ)言真是得心應(yīng)手,繁則極盡秾艷,簡(jiǎn)則極盡洗練,一律應(yīng)付自如。張愛(ài)玲一并展示了中國(guó)小說(shuō)和中文最美的收獲。
《茉莉香片》《心經(jīng)》《金鎖記》《年青的時(shí)候》《花凋》《紅玫瑰與白玫瑰》,還有《傾城之戀》的一部分,都屬于“心理分析小說(shuō)”。這路小說(shuō)的核心是心理先于現(xiàn)實(shí)。一切都起始于頭腦之中,人物為一個(gè)或簡(jiǎn)單,或復(fù)雜,或起初簡(jiǎn)單而后變得越來(lái)越復(fù)雜的念頭所驅(qū)動(dòng),在自己的內(nèi)心世界左右奔突,尋求出路;外部世界不過(guò)先是為此提供必要條件,而后轉(zhuǎn)化成為阻遏,以及進(jìn)一步所施加的壓力。
止庵談外國(guó)文學(xué)
阿爾志跋綏夫
阿爾志跋綏夫并不是思想家,只是對(duì)于所處時(shí)代敏感到了病態(tài)程度,并把自己的感受寫(xiě)得淋漓盡致而已。
納博科夫
納博科夫移居美國(guó)多年,此前他只在俄國(guó)流亡文學(xué)的小圈子里享有名聲。《洛麗塔》改變了這一切。從此他成了焦點(diǎn)人物,無(wú)論在美國(guó),還是在全世界。
他所以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首先因?yàn)橹橇Τ骸<{博科夫從本質(zhì)上講是個(gè)開(kāi)玩笑的人,但是他把玩笑開(kāi)得比一切都更真實(shí),更復(fù)雜,也更深刻。《洛麗塔》就是好例子。
卡爾維諾
卡爾維諾與眾不同之處,他自己講得清清楚楚。用心寫(xiě)作訴諸情感,用腦寫(xiě)作發(fā)揮想象。
想象本身已經(jīng)足以給人類提供永恒的價(jià)值取向,而并不在乎這一想象的意義何在。換句話說(shuō),想象與我們的存在之間并不是派生或隸屬的關(guān)系,它既非譬喻,亦非修飾,不能用存在來(lái)界定;它本身就是獨(dú)立的存在,已經(jīng)具有終極意義。
芥川龍之介
談到《今昔物語(yǔ)》,往往要提芥川龍之介。因?yàn)樗男≌f(shuō)頗有些出典于此,他對(duì)這書(shū)的評(píng)價(jià)也最到位。
《今昔物語(yǔ)》與芥川小說(shuō)相比,其一簡(jiǎn)潔,其一糾纏;其一明快,其一晦澀;其一坦蕩,其一惶惑。我們無(wú)須指定孰高孰低,孰是孰非,亦無(wú)從舍此取彼。
作家所能給予我們的,或許就是某一刻的共鳴,這個(gè)共鳴或許稍縱即逝,說(shuō)長(zhǎng)不長(zhǎng),說(shuō)短不短。15萬(wàn)字,20余位重要作家,只需要一個(gè)下午的閱讀時(shí)光,即可盡收囊中。
編輯:李耀榮
原標(biāo)題:止庵丨讀書(shū)最大的益處,是使我成為我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