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的幸福觀沒有抽象的哲學思考,只有深入淺出的經驗之談。正如他所說,他不是以哲學家的身份去研究何為幸福,而是以遭受世界苦難的普通人的身份去書寫,他謀求的乃是改善世界的生存狀況,表達出世人謀求幸福的心聲。
2020年的今天,比之100年前的人們,我們的困惑一樣都沒少,反而加倍遞增,羅素富有實踐意義的幸福觀穿過歲月的屏障,依然擲地有聲。
如何化解現代人的精神疲憊?

《幸福之路》,[英]羅素著,傅雷譯,上海南國出版社,1947年4月版。這是羅素《幸福之路》最早譯介入華的版本。
何為幸福?歷史上的哲學家對這個問題看法不一。對于伊壁鳩魯學派來說,人只有去掉靈魂中不必要的欲望,才能幸福;在斯多亞主義者看來,剎那幸福即是永遠幸福;在康德那里,幸福是“對自己的狀態的滿足”,又與內心的道德律令息息相關;對加繆來說,幸福就像西西弗斯那永遠無法抵達的終點。從亞里士多德到康德,從叔本華到加繆,再到后現代的理論家們,對幸福的思考幾乎伴隨著整個西方哲學史,幸福問題是哲學家們思考最多的問題之一。
羅素批判性地繼承了伊壁鳩魯、亞里士多德等哲人的幸福思想,并提出了自己的幸福觀。他對幸福的思考,貫穿于對政治和宗教的思考中;他對幸福的追問,也奠定了他的道德哲學體系。
羅素的幸福觀集中體現于《幸福之路》一書中,他寫下此書時,正是20世紀30年代,那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盡管人們的生活早已駛離了上帝宰制的碼頭,然而,人們所謂的“幸福”還是和對上帝的信念息息相關,羅素批判壓抑人性的宗教道德準則,認為人之幸福未必與宗教信仰有關;與此同時,面對工業的發展,一戰的滿目瘡痍,羅素開始思考人之幸福的要素。羅素對幸福問題的重視,與他對宗教和政治的思考,以及他的反戰經歷緊密相關。
在羅素看來,現代人不幸的來源有兩個,一是社會制度,二是個人心理。社會制度問題不是羅素幸福觀談論的重點,相反,羅素認為,人的不幸福往往來自錯誤的倫理觀、道德觀和思維習慣。羅素認為,有時壓倒人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大問題,而是小情緒。現代生活節奏之快,競爭之過度,常常令人有倦怠感,除卻身體的疲憊,精神疲勞才是困擾人的主因。羅素認為,現代人的精神疲勞主要由焦慮引起,面對一時無法解決的問題,人們總是輾轉反側,殫精竭慮,陷入焦慮的漩渦,卻無法徹底解決問題。羅素認為,現代人之所以如此,一是因為操心已成為現代人的習性,另外,則是因為人們不愿面對恐懼,直面困境。在現代人焦慮的問題上,羅素提倡一種精神自律,他認為,人們應該真正直面問題,嘗試找到解決辦法,不然就暫時放下,過多思考反而于事無補。
如果說在解決焦慮的問題上,羅素的辦法有些老生常談,那么他對煩悶的看法則頗為深刻。在羅素看來,消極情緒不一定都是壞的,煩悶的對立面不是歡愉,而是興奮。為了緩解煩悶,人們縱情聲色,無止境地找樂子,然而,“越是隔夜過得好玩,越是明朝顯得無聊”。在羅素看來,煩悶未必不是好事,煩悶是沉靜生活的前奏,是偉大生活的標志。
他在《幸福之路》中說,“一切偉大著作都有乏味的部分,一切偉大生活都含有乏味的努力。”哲學家蘇格拉底和妻子的生活一成不變;康德的生活高度自律,他一生的活動空間就是自家的方圓十里。“安靜的生活是大人物的特征,他們的喜樂也不是外人心目中認為興奮的那種生活,一切偉大的成就必須歷經不懈的工作,其精神專注與艱難程度,使人再無心思去適應狂熱的娛樂”。面對現代人的煩悶,羅素不提倡無節制的刺激和興奮,而希望人們找到貼合興趣的事業,去尋找長久而高質量的歡愉。
對于現代人熱衷的旅行,羅素也表達了他的看法,“太多旅行,太多復雜印象,不適合年輕人,縱使他們的成長不再寂寞,殊不知唯寂寞才能生產果實……不能忍受煩悶的一代,必定是渺小的一代”。羅素并非排斥消遣,但在他看來,無節制的娛樂往往會令人麻木,學會沉淀,忍耐煩悶,為生活留下一方空白的天地,才是可取的。
幸福是自我與他人、與環境的平衡

羅素與第二任妻子多拉·勃拉克看孩子們嬉戲。盡管羅素大談“幸福哲學”,但他本人肆無節制的社交生活卻給多位女性帶來不幸。在他與第二任妻子多拉結婚之前,他先是勾引有夫之婦奧托琳·蜜樂兒夫人,因此拋棄了發妻愛麗絲。在與奧托琳發生關系的同時,他又與海倫·達德利發生關系,始亂終棄,并導致后者精神失常。拋棄海倫后,他又同時分享蜜樂兒和克萊特兩位女性對自己的愛情。直到1920年,他投入了更年輕、更富有魅力的多拉·勃拉克懷抱中。但隨著多拉發現羅素私生活中越來越多不檢點之處,兩人的婚姻也迅速走向破裂。羅素不僅趁多拉不在家時與負責教導孩子的家庭女教師同床共枕,還惦記上了自己的學生皮特·斯彭斯。皮特后來擠掉多拉,成了羅素的第三任妻子。在與羅素的多年相處后,多拉如此評價自己的前夫羅素:“盡管他熱愛民眾并為他們的苦難感到痛苦,但他依舊遠離他們,因為他身上有貴族氣質,同平頭百姓缺乏聯系……他一生中會傷害很多人,他最大的悲劇性缺點,是很少感到歉意”。
亞里士多德認為,幸福是“靈魂合乎完滿德性的實現活動”,在政治生活、享樂生活與沉思生活之間,他認為沉思生活才最為幸福。與亞里士多德相比,羅素的幸福生活不是哲人的幸福,而是普羅大眾的幸福,這種幸福包含著關系性的善。對于羅素來說,幸福的秘訣是“讓興趣盡量擴大,對人對物的反應,盡量傾向于友善”。換句話說,人只有認清自我在人群中的位置,保持自我與他人、與環境的平衡,自利利他,才有幸福的可能。
羅素認為,人們無法擺正自己與他人、與外界的關系,缺少自知之明,這往往成為煩惱之源。他批評了幾種類型的人,一種是罪惡感太強的人,他們是“體面的罪人”,因為害怕成為人群中的邊緣人,他們嚴格遵守清規戒律,過度自省,到頭來使生活毫無樂趣可言。羅素在《幸福之路》中說,“在如此廣大的宇宙中,他覺得最重要的莫如自己的有德,鼓勵這種特殊的自溺,是傳統宗教所犯的最嚴重的錯誤。”羅素批判壓抑人性,有禁欲色彩的宗教道德準則。在這一點上,羅素與邊沁和西季威克是類似的。邊沁認為幸福是以個人利益為前提的,而對西季威克來說,道德準則應建立在人們追求最大快樂的基礎上。
過于苛責自己的人往往會變得不快樂,相反,過于苛責他人,也毫無幸福可言。羅素還談及一類人,那就是受虐狂。受虐狂不是苛責自己,而是苛責他人,他們往往夸大自己對他人的友善,希望自己的仁慈會贏得掌聲,一旦沒有收到他人的感激,就自怨自艾。羅素認為,自虐狂往往在單純的事情上附加了太多價值,過于高看自己的價值。然而,過于自責的人和受虐狂卻有相通之處,他們都過于在乎外界的評價。羅素認為,解決之道在于,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認識到自己的動機并不那么舍己為人。正確估量自己,才有幸福的可能。在自我與他人、與外界的關系上,罪惡感強的人和受虐狂走到了人際關系的兩極。
人如何看待自己,決定了自我與他人的關系,不僅如此,人還要面對人群,面對大眾組成的輿論。薩特說,“他人即地獄。”羅素在面對公眾輿論的問題上態度堅定,他認為,人若想得到幸福,必須設法逃避輿論的專橫。一個人在人群中顯得孤獨,未必是其本人的過錯,人不應局限于一時一地的既成觀念,也不一定要與環境相一致。因為在羅素看來,輿論的聲音未必理性,反而成為束縛人個性的桎梏,甚至成為殺人的利器。
在個體對輿論的看法上,羅素突出了環境對人之幸福的重要性,人要選擇與自己觀念大體一致的環境,有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人或許無法改變環境,但在面對輿論的時候,要堅守自身一方獨立的精神空間,因為“幸福的要素是,我們的生活方式必須源于我們自己的深邃沖動”。
幸福是人之欲求滿足的結果?
普里莫·萊維曾說,“每個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遲早都會發現,完美的幸福是無法實現的。”也許,人們越是祈求完美的生活,也就離幸福越遠,相反,幸福的實現卻需要一定程度的匱乏。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人的本質與動物有著內在的連續性,匱乏是動物乃至人活動的本質特征。正因匱乏,人才會不斷地有欲求,而幸福,某種程度上是人之欲求滿足的結果。然而,在羅素看來,當人憑借財富毫不費力地滿足自己的欲求時,快樂也會隨之消失。
幸福,不是無事的完滿,而是拼搏后的獲得。現代生活中,競爭成為人們生存的常態,羅素并不反對人們為了幸福生活而去努力,但他反對過度競爭。在羅素看來,現代人的競爭往往不是為生存的競爭,而是為成功的競爭,而衡量成功的標準卻日益單一。當金錢取代了傳統的職業榮譽,成為衡量一切職業的成功標準時,人們生活中的其他維度都變得黯然失色。
現代性精神是一種永恒的緊急狀態,更新、更快、更好、更完美的生活是現代性的永恒追求,這意味著其間的個人永遠在追求著更高層次的“成功”,然而,“持續不斷地加速變得不可避免,結果勢必是停滯與潰敗。”羅素并不是反對競爭,而是反對人們過度競爭而喪失了工作的樂趣,一味以金錢作為衡量標準而忽略了對卓越的追求。面對過度競爭,羅素提倡人們走出自己狹小的天地,培養一些“無用的樂趣”,在追求世俗的成功之余,給自己留下一方恬靜的天地。
凡事不可過度,是羅素幸福觀的一把標尺。幸福不是短暫的刺激,而是長久的樂趣,不是過度的競爭,而是對卓越的追求;幸福,是個體與他人、與環境的一種平衡狀態;幸福不在于無限的追求,而在于適度的留白。“須知參差不齊,乃是幸福本源”,幸福,需要恰到好處。
編輯:李耀榮
原標題:100年前,羅素的“幸福觀” 如何撫慰現代人?







 廣告
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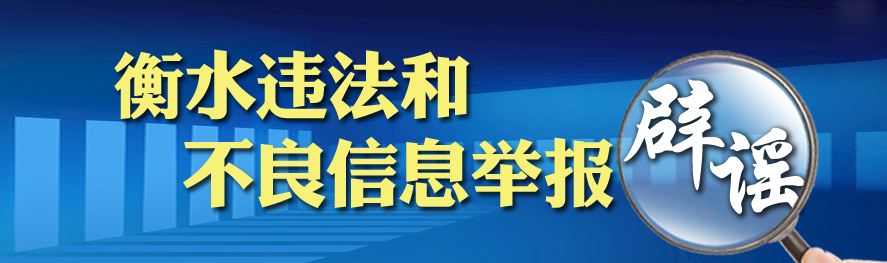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