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劉禹錫一句詩,奠定了洛陽牡丹的國花地位。其實牡丹故鄉在菏澤,只是一則故事火了洛陽牡丹。
先說故事上篇。當初武則天一怒之下,將牡丹貶至洛陽,未曾想反倒是成就了她。可是話又說回來,在那個大雪紛飛的隆冬之夜,武皇醉筆寫下詔書:明朝游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百花懾于此命,夜里競相開放。只有牡丹敢于抗旨不開,這樣不媚上不唯權的底氣,自然當得起國花之名。如此看來,到底還得是她自己成就了自己。
牡丹在我國栽種培育的歷史可上溯到南北朝時期,《嘉記錄》《太平御覽》等文獻均有記載。至隋唐時已繁盛無比,蔚為大觀。李白的《清平調》三首,即是借著描寫形色各異的牡丹贊美楊玉環,從而取悅了明皇而得以專享高力士脫靴的尊榮。《龍城錄》中記有一人:洛人宋單父,字仲儒,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異千種,紅白斗色,人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召至驪山,樹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余兩。內人皆呼為“花師”,亦幻世之絕藝也。此人沒有李白的沖天才氣,也便沒有詩仙那樣坎坷的求職經歷。可他僅憑能種牡丹,就輕而易舉地贏得了玄宗的青睞,被授予“大唐花師”的光榮稱號,榮耀一生。
五年前的四月,我和愛人去洛陽賞牡丹。一出站口,滿目鮮花著錦,一城焚香欲燃,每到一處,都教人神魂顛倒,如同飲了一盞“千紅一窟”。納罕之余查閱資料方知,如今牡丹的花色品種已不可勝數。僅從顏色一項試舉幾例,便可以感受到牡丹的美輪美奐。譬如,醉酒楊妃、飛燕紅妝、出水洛神、貂嬋拜月、二喬、金屋嬌等,幾乎將古代美女囊括其中。最值得費一番筆墨者名喚綠珠墜玉樓。此牡丹潔如玉脂,每片花瓣的中間都有一顆碧斑,恰似綠珠墜入玉液瓊漿之中,令人不由想起西晉美人綠珠姑娘。這牡丹簡直美得不可方物,但是在我看來,這款命名卻是殘忍得很。綠珠姑娘自小才貌出眾,卓然不群,在青春正好的年紀,被洛陽土豪石崇納為愛妾,這幾乎是她無法擺脫的命運。石崇能在史上留名,皆因他勇于和王愷斗富。石崇并非簪纓世家,在極其講究門閥的魏晉很難出人頭地。但他因為有錢,在追求及時行樂、窮奢極欲的晉代照樣可以無限風光。這樣一個依靠搜刮民脂民膏、聚斂財富的地方官員,除了借用綠珠的美貌來裝點門面、夸豪競奢之外,他會給到綠珠一絲一縷的精神之愛嗎?綠珠姑娘長年禁錮在金谷園中,豢養如寵物,被惡俗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間,這可曾是她想要的生活呢?說這個史載“殺妓侑酒”、床邊常備“肉屏風”“肉痰盂”的男人惡俗真是輕饒了他,綠珠一天天都在目睹著他的丑陋與罪惡,體味著他的卑鄙和暴虐,她怎么會像史家講的那樣,為了表示對石崇的忠貞不渝,在孫秀闖進金谷園時而選擇縱身一躍呢?我同意夏堅勇教授的解析,綠珠是因絕望而死。她的死“是一種解脫,也是一種抗爭——向丑惡的男性世界的抗爭。可惜這種抗爭卻被后人善意地曲解了,硬是給她樹了一塊‘殉情’的貞節牌坊。” “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墮樓人。”在所有吟詠這段往事的詩詞中,杜牧《金谷園》于凄婉中發出了繁華易散的感慨,大約是最接近綠珠墮樓時孤絕悲涼的心境的。
將牡丹比作美人,詩詞之中并不鮮見。可是借用牡丹的美來警省亡國之君,好像歷史上僅有一例。宋僧惠洪《冷齋夜話》中講了一則小故事。宋軍大舉南下,飲馬長江。可是金陵城中后主李煜仍在賞月觀花,詩酒歌舞。法眼禪師看到御苑中盛開的牡丹,作牡丹詩偈有句:發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何須待零落,然后始知空。無奈后主省悟不到花容難駐、嬌艷不常的警示,依舊沉湎聲色,茍且偷安,終至金陵城破,肉袒出降。身為亡國之君,囿于汴河一隅,追思當年的牡丹詩偈,后主的詞自此得以從花前月下轉入了故園山河。王國維《人間詞話》:詞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國色天香的牡丹,借李煜之目助推了危如累卵的南唐小國的覆滅,同時也借李煜之手將詞推入了一個更為深摯宏闊的境界。
再說故事下篇。剛強不屈的牡丹一到貶謫之地,便在洛陽烈火烹油般昂首怒放,無拘無束,無遮無攔。這更加激怒了武則天,她敕令用火燒死牡丹。翌年春天,枝干雖被燒焦的牡丹反而開得云蒸霞蔚,春色無限。武則天這才見識到牡丹的矢志不移,敬佩牡丹的焦骨剛心。而千百年來,無數詩人墨客的筆觸只是停留在牡丹“形色香”的表面,這實在是風骨牡丹的悲哀。明代俞大猷《詠牡丹》:閑花眼底千千種,此種人間擅最奇。國色天香人詠盡,丹心獨抱更誰知。俞大猷為明代抗倭名將,與戚繼光并稱“俞龍戚虎”。他的奇節與抱負也只有牡丹獨守丹心差可比擬了吧。
行文至此,不得不說到《牡丹亭》了。“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朝飛暮卷,云霞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船,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殘……”無論何時聽到這段《皂羅袍》,我都在大美中聽聞出了大悲,那真是一種無可名狀的情愫。“無可名言,但有慚愧。”作為寫作之人,我不得不飽嘗此種遺憾。但我也同樣慶幸,這般神啟似的感覺并不會光臨世上的每一個人。
湯顯祖是一個十足的理想主義者。他潔身自好,不諳世情,二十一歲中舉之后婉拒權相拉攏,致使空負才名,屢試不第。萬歷十一年張居正死后,湯才子終以三十四歲高齡得中進士,到南京賦了八年閑職。萬歷十九年,他因目睹官僚腐敗憤而上《論輔臣科臣疏》,觸發圣怒而貶為地方小吏。在浙江遂昌,他“云鉗剭,罷桁楊,減科條,省期會,建射堂,修書院”,勸農桑,施善政,使得浙中偏僻貧瘠之地大為改觀。遇赦一年的他把這里看作了自己的理想王國。他為實施自己的政治主張一無顧忌,擅自釋放獄中囚犯回家過年,準許他們元宵節陪同家人上街觀燈。如此富于理想,怎能為官場所容?一旦政敵把柄在手,暗箭冷槍射來,理想破滅的湯才子即時潰不成軍。那是萬歷二十六年,四十九歲的湯顯祖一紙辭呈,揚長而去。他坐回家中窗前,將畢生理想化作錦繡文字,一筆一畫,注入起死回生的情愛傳奇之中,著成了戲劇史上“前無作者,后鮮來哲”的“玉茗堂四夢”。
《牡丹亭記題詞》曰:“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有此一語,天下情愛盡矣。我寫愛情故事,被讀者僭稱為“中國最會講故事的癡情大叔”。我以為,只有湯臨川方可擔得此名。
作者: 賈九峰 編輯:李耀榮







 廣告
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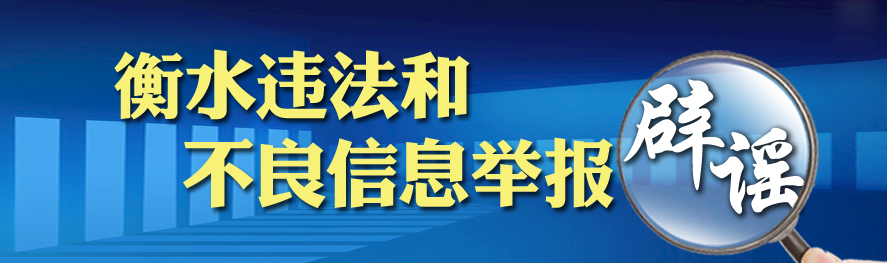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